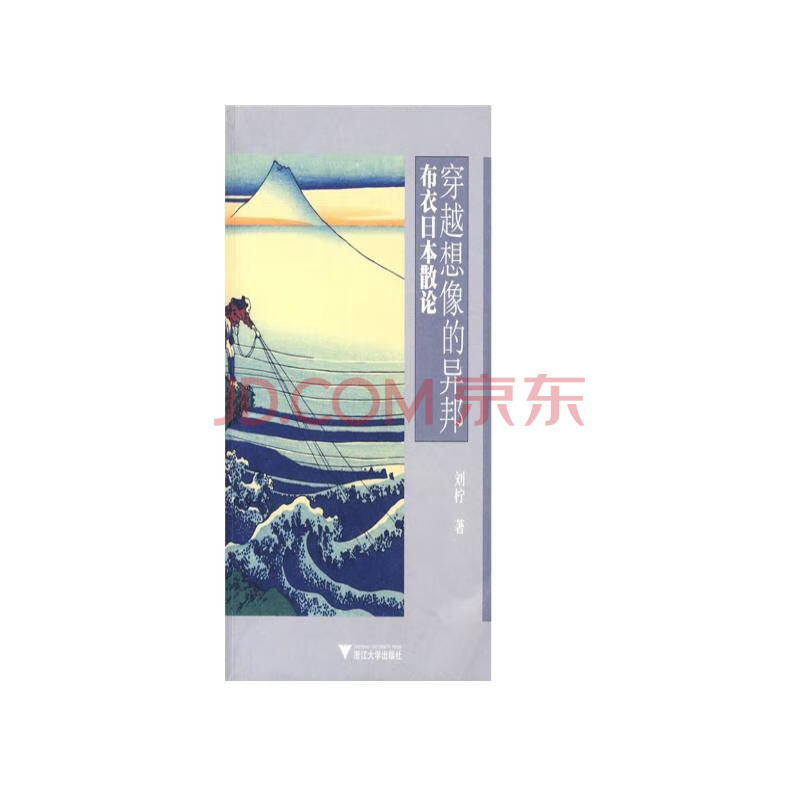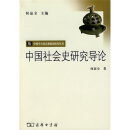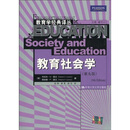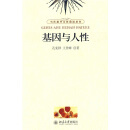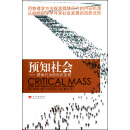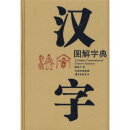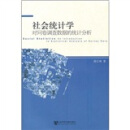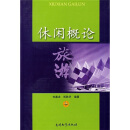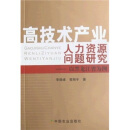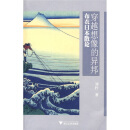内容简介
《穿越想像的导邦布衣日本散论》从现状的观察切人,立足于文化和国民的社会心理,力求从传媒视野和历史背景的纵横交错中复原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本来面貌,以期校正国人长期以来审视邻国时建基于某种想像之上的、不无误读的、飘忽不定的照准。进入21世纪,日本急剧转身,原本就难以捉摸的神秘国度在世人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其定位与国家战略的“调整”,不可能不在社会、国际关系、国民历史观、文化及舆论环境上投下影子。
经常书评
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游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场,数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十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四海皆兄弟。
——著名搬日作家·李长声
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刘拧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
目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日本版NSC:首相官邸“白宫化”的重要步骤
日本离核国家有多远?
日美同盟有“隙”?
福田访美:蜜月同盟的拐点?
“价值观外交”何以超越国家利益冲突
东亚一体化:谁主沉浮?
日本幢幢谍影的背后
现状的日本:从容与焦虑
“活力门”骚动的背后
“赛先生”:酷日本的软实力
日本城建进入环境生态学时代
走向民生大国:21世纪日本的生存之道
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两个问题
日本的恶心
派阀:自民党政治的秘密
“下流”,怎么了?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大国化”焦虑下的舆论环境
“命令放送”与报道自由
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出版史的良心记录
何谓新闻记者
日本出版的四种“神器”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
新闻界与政治
历史中的日本:何以超越?
激荡的百年史,现实的掌舵者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
要同盟,还是要参拜?
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漫长的战败
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
宫泽喜一:“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超越误读
中日有多远
对华强硬的背后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困境
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图存
“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
作为文化的日本
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本的传统有多厚
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叶隐闻书》、武士道及其他
哈“不良”
我跑,故我在
日本漫画:冷酷仙境的冒险
漫画?动漫?宅男
日本人到底爱不爱撒谎
服饰的表情
知日当如李长声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
后记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
试读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2007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是现行的“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的日子。60年一甲子,一部身世奇特的宪法风雨兼程地走过,虽未经任何修改,但核心部分却被空蚀,呈空心化——日本宪法正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改,还是不改?是一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空前的论战。正值国民纷纷涌出国门、踏上海外之旅的黄金周,各大主流媒体推出与此相关的报道、社论、民调连篇累牍,给人一个总的感觉:改宪问题已到了须臾不可放置的节骨眼上。
何谓“和平宪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随后,美军对日本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作为美对日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废除基于天皇总揽统治权的《明治宪法》,制定一部从制度上根除历史旧恶、“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法成为当务之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责令盟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草拟出宪法草案,并提出了制宪三原则:第一,天皇的权力和义务由宪法予以规定,天皇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责;第二,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不但要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也要放弃作为自卫手段的战争,把防卫事务委托给“左右世界的崇高理想”;第三,废除封建制度,除皇族外,华族权利只限于本人一代,不保留任何特权。
惠特尼准将不负所望,很快拿出了宪法草案,于1946年2月13日交付日本政府“检讨”。日本政府对于以象征天皇、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为主体的宪法草案,表示难以接受。而美占领当局则考虑抢在2月26日国际“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将宪法既成事实化,避免委员会成立后插手制宪事宜。因此,以高压手段逼迫日本政府接受,限期48小时内作出答复,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草案,占领当局将单方面向日本国民公布。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只有表示原则接受。在议会审议之后,于1946年11月3日以《日本国宪法》的名义颁布,并于次年5月3日起实施。可以说,日本是在接受美援的脱脂奶粉和压缩饼干的同时,被迫接收了“和平宪法”。某种源于被“强加”的郁闷和反弹,构成了战后一直绵延至今的改宪思潮的主调。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于对冷战的应对和反共的战略需要,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彻底打碎战争机器的“非武装化”、“民主化”,跳跃到后来重新有限度地武装日本,从而埋下了后者对战争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反省不彻底的病根,而前者“首鼠两端”的政策权宜性,也为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改宪派”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
何以是现在
日本作为东西方冷战最前沿的桥头堡,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左、右翼思想尖锐对立,各种政治势力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所有这些“左”与“右”的思想交锋,本质上几乎都能以“护宪”与“改宪”为线索贯穿起来。这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社会,但这两种思潮的博弈是如此的激烈、持久,乃至其他的声音都湮没无闻了。
事实上,自“和平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改宪”的论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不仅如此,其间还几度形成高分贝的动议,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性事件。1970年11月25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4名“盾会”(由三岛弟子组成的、效忠其个人的准军事化右翼团体)成员闯入陆上自卫队营地,绑架东部方面总监益田兼利,召集千余名自卫队士官宣读“檄文”,呼吁改宪,发誓用血和生命来捍卫“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最后愤而切腹自戕,以唤起“国民精神”的觉醒。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三岛由纪夫现象”成为日本国内长久的话题,而事件本身,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改宪”一度成为禁忌。
对宪法问题,日本战后历届内阁,几乎都采取回避策略。继在安保斗争中下台的岸(信介)政权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曾公开声明,“在自己(首相)任内不修改宪法”。其后,直到小泉内阁为止,前后18任首相,无一例外,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表态——首相任内不轻言改宪,成了永田町约定俗成的惯例。
首先打破这种“惯例”的,是安倍。而安倍的政治基因,则来自其毕生尊崇的外祖父岸信介的遗传。作为不折不扣打着改宪牌上台的政治家,安倍从不掩饰其政治保守色彩,谈到宪法问题时,言必称“摆脱战后体制”,这与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当过阁僚,1957年作为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后创设“宪法调查会”,始终为改宪而不懈奔走的外祖父半个世纪前念兹在兹的“占领后遗症的根绝”、“真正独立的恢复”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即使安倍,也深知改宪之水甚深,不仅需要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要应对居高难下的法律门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就。连能让自民党乾坤翻转的政治强人如小泉者,也只是从释法人手,先把兵派出去,然后再试图从舆论上政治正确化,但却始终未触碰程序性法案。
而安倍上台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