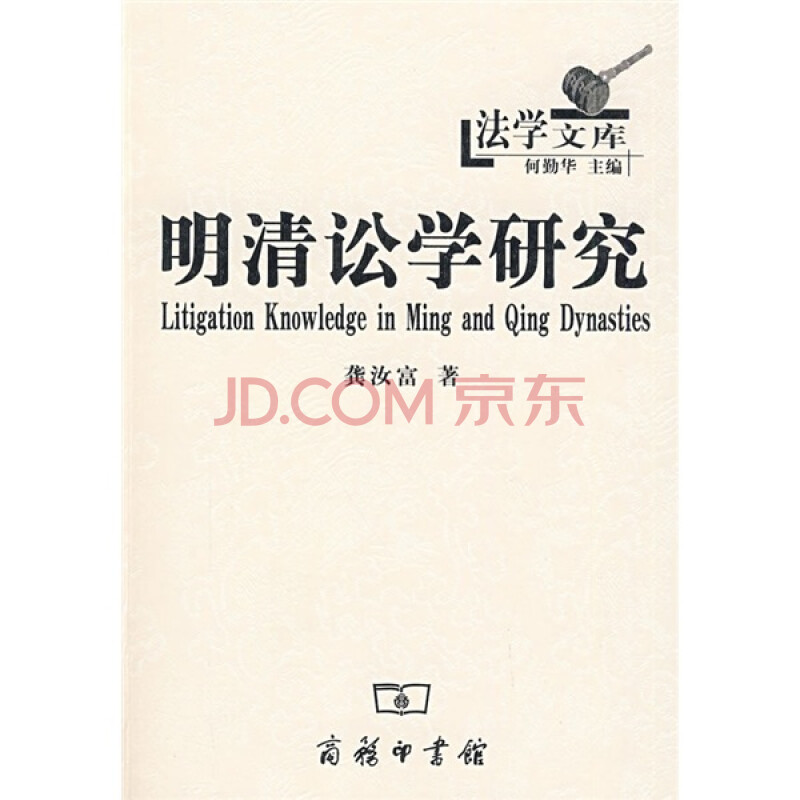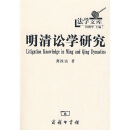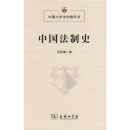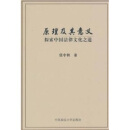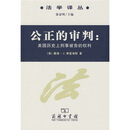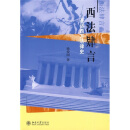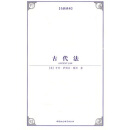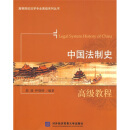内容简介
明清时期,以讼师秘本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讼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讼学以落魄文人为职业群体,以乡村百姓为主要传播对象,采摭律学成果,杂以刀笔珥语,假以公案判例,提炼撰状技巧,兼容合成为一种诉讼攻防之术.它根植于乡土社会,表达了基层民众的话语方式,满足了民间纠纷诉讼常备的法律知识,激发了乡村民众的诉讼热情,不仅冲击了中国古代无讼观的价值理念,并对地方司法体制形成潜在的挑战。尽管明清讼学一直受到官方的排斥和打击,但它仍然以各种隐秘的方式存在着,并填充了正统学问所不备的诉讼实学的真空,成为民间日用应酬常识的草根法学,为了解我国古代乡村民众的法律知识形成及其处置纠纷的基本技巧,提供了生动例证。
精彩书摘
第二章 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与传播<br> 第一节 民间法律知识形成的主要渠道<br> 一、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br> 法学的存在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怎样把制度化的行为规范诠释为日用常识,使之一目了然,进而潜移默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人格养成。因此,越是接近民众生活的法律学问,其宣传和教育的方法就越是显得通俗平实和丰富多彩。我国古代统治者对于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一直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法律是明主治国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但又是圣人所“不尚”且应哀恤敬慎的“无冤刑祥”。这种整体法律价值观的评估实是源于传统儒家正统思想对人性论的基本回答:性善欲恶论决定了对个人必然要去恶从善,而对于群体则要消除害群之马,弘扬正气。善与恶、礼与刑、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君子与小人等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封建治道的基本框架,因而法律在其适用上存在差别,本身就体现了人性论在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判断。与法律价值观相适应,我国古代现实司法中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范式,即秉公执法、除暴安良的衙门老爷总是在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权衡,稍微偏失其中一端,即招来天怒人怨,也为国法所不容。另一方面对于法律与民众的现实关系,强调要广为教谕,使之周知易晓,反对不教而诛。但通观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法律体系越是完备复杂,越是远离百姓的视野。在获得法网“密而不漏”的好处同时,民间法律事务不得不求助于诸如“讼师”之类的非法的“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化的前提正是法律体系在日益复杂繁密之时,却远离了民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乐意看到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者来分享法律资源和尊严权势,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封建统治者总是想一相情愿地开展一项十分有趣的教化工作,把日益丰富的法律内容压缩成更简单的生活和处事规则,使老百姓耳熟能详,而漠视日渐复杂的财产关系正促使人们不断增强捍卫财产权利的意识。尤其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如何让老百姓熟悉和接受日益庞大复杂的律例体系,而又尽量减少甚至消除“讼师”对民间法律事务的非法干预,加大法律宣传与教育力度势在必行。通过接触丰富的历史材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无论政府和民间,在传播法律知识和开展法律教育方面,的确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花费了不少心血,做出了一些成绩: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br> 重视法律的宣传与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周礼。秋官。大司寇》中就讲到,每年“正月之吉”,大司徒、乡大夫要向民众悬法、颁法,其后州长、党正、族师每年分别向属民“读法”二、五、十二次,闾胥甚至每逢集会就向群众“读法”;经过儒家改造过的《周礼》当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我国自古以来由乡党什伍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却一直存在着集体教化、申明功过的传统,此即后来乡约保甲之祖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官府垄断法律知识和教育资源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人诠释法律并且讲学授徒的现象。“造竹刑”并教学生“执两可之说”的邓析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职业者”。据《吕氏春秋.离谓》所载,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在我国封建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看来,邓析也是教唆词讼的讼师鼻祖。但无论怎样评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他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显然是非常迫切的事情。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方针。法条成为教材,法吏成为楷模,不可谓不重视法律,但终因法令繁密、民无措手足而二世遂亡。秦汉之际,刘邦鉴于秦朝刑法“密如凝脂”,便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实际上就是以最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与老百姓当时最切近和最起码的法律要求。不仅如此,加强各级官吏学法用法,也是十分迫切的。三国魏明帝时,卫觊就曾认为“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并建议。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律博士之设反映政府已经开始把官僚学习法律知识摆到了议事日程。但到隋代,由于出现个别律博士玩法弄律,舞文作弊,隋文帝将律博士和部曹明法、州县律生一并停废。尽管当时人们不可能思考到道德风险问题,但从整个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阶层是否能忠实于法律和民众,已经开始受到怀疑。制定贴近民众的简洁明快的法律让更为广泛的人群学习掌握,不失为治道之先筹。律法简约是我国古代立法的基本要求,如被称为我国古代法典瑰宝的唐律就是以科条简约而闻名,其中已经蕴含着方便老百姓知法守法的深刻用意。<br> 明代朱元璋在阅览《律令直解》时,对大理寺卿周祯等人反复叮嘱:“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产晓。”“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洪武十九年五月,为申明游民之禁,“命户部板刻训辞,户相
目录
序<br>绪论<br>一、讼学<br>二、选题<br>第一章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诉讼的价值理念<br>第一节 诉讼的内涵与释义<br>一、“讼”之含义<br>二、“讼”之解析<br>第二节 鼠雀之讼与甘棠理念<br>一、鼠有角,雀有牙<br>二、甘棠听讼<br>第三节 健讼、速讼与息讼的现实基础<br>一、珥笔健讼<br>二、讼贵速决<br>三、息讼有道<br>第二章 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与传播<br>第一节 民间法律知识形成的主要渠道<br>一、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br>二、官方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br>第二节 从邓析到哗鬼讼师、恶讼师<br>一、邓析之徒<br>二、鬼恶讼师<br>第三节 从《邓析子》、《公孙龙子》到《邓思贤》、嚷公理杂字》<br>一、《邓析子》与《公孙龙子》<br>二、《邓思贤》与《公理杂字》<br>第四节 讼师的寄托空间<br>一、书铺、酒肆与茶馆<br>二、歇家与私塾<br>第三章 明清法律职业与讼师形成之考察<br>第一节 明清士人出路歧异与法律角色<br>一、士人多歧路<br>二、士绅的法律角色<br>第二节 刑名师爷与讼师的职业异同<br>一、刑名师爷<br>二、刑名师爷与讼师的博弈<br>第三节 讼师队伍的层次考察<br>一、讼师之恶<br>二、良恶有别<br>第四节 职业讼师的标准及其流变<br>一、业余讼师<br>二、职业讼师<br>第四章 讼师秘本的制作及其基本内容<br>第一节 讼师秘本的基本特质<br>一、流传诡秘<br>二、取名玄乎<br>三、语言夸张<br>四、内容雷同<br>第二节 讼师秘本制作:经验与素材<br>一、讼师秘本的经验来源<br>二、讼师秘本的素材来源<br>第三节 现存讼师秘本的版本和内容述略<br>一、夫马进等人的研究<br>二、补充若干版本<br>三、讼师秘本的主要内容<br>第五章 讼师秘本与其他法律著作之比较<br>第一节 讼学的主要载体<br>一、构讼之书<br>二、讼师秘本对法律的解读<br>第二节 与律学著作之比较<br>一、立场地位<br>二、价值观念<br>三、解释法律的方法<br>四、设定的读者群体<br>第三节 与刑幕读本之比较<br>一、秘密与公开<br>二、注重程式与意在决胜<br>三、诠释规则与夸大其词<br>四、富有个性与千篇一律<br>第四节 与案例判牍之比较<br>一、判牍中的情理法<br>二、讼师秘本对情理法的利用<br>第五节 与公案传奇之比较<br>一、公案传奇中的法律内容<br>二、与讼师秘本的内容关联<br>第六章 讼师秘本对法律的理解及其技巧<br>第一节 诠释律例的一种灵活方式<br>一、本诸情理<br>二、贴近生活<br>三、别出心裁<br>第二节 理解法律的角度、目标与方法<br>一、致君泽民<br>二、奇正相生<br>三、解律有法<br>第三节 讼师秘本的逻辑<br>一、装点情理<br>二、以轻作重<br>第四节 出奇制胜的诉讼技巧<br>一、讼不轻举<br>二、智烛机先<br>第五节 讼师秘本常用术语<br>一、技巧术语<br>二、写作技巧<br>三、语言技巧<br>第七章 明清时期国家对讼师秘本的厉禁<br>第一节 讼师、讼师秘本、讼学对明清社会的冲击<br>一、坏人心术,诱导险诈<br>二、信口雌黄,破坏团结<br>三、费时荒业,破产倾家<br>四、嚣讼公堂,拖累官府<br>第二节 明清时期国家对讼师与讼师秘本的认定<br>一、讼师的身份认定<br>二、讼师秘本的认定<br>第三节 明清时期国家对讼师秘本与讼师的查处一<br>一、天网恢恢,疏而有失<br>二、多管齐下,严厉打击<br>第八章 明清讼学对司法制度的影响<br>第一节 提高了民众的法律知识<br>一、民间法律读本<br>二、诉讼历练<br>第二节 刺激了民众参与诉讼的热情<br>一、诉讼纠纷日增<br>二、从业者相习成风<br>三、家族团体诉讼盛行<br>四、讼案屡拖难结<br>第三节 对封建司法制度的潜在挑战<br>一、积案难清<br>二
试读
第二章 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与传播<br> 第一节 民间法律知识形成的主要渠道<br> 一、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br> 法学的存在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怎样把制度化的行为规范诠释为日用常识,使之一目了然,进而潜移默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人格养成。因此,越是接近民众生活的法律学问,其宣传和教育的方法就越是显得通俗平实和丰富多彩。我国古代统治者对于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一直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法律是明主治国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但又是圣人所“不尚”且应哀恤敬慎的“无冤刑祥”。这种整体法律价值观的评估实是源于传统儒家正统思想对人性论的基本回答:性善欲恶论决定了对个人必然要去恶从善,而对于群体则要消除害群之马,弘扬正气。善与恶、礼与刑、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君子与小人等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封建治道的基本框架,因而法律在其适用上存在差别,本身就体现了人性论在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判断。与法律价值观相适应,我国古代现实司法中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范式,即秉公执法、除暴安良的衙门老爷总是在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权衡,稍微偏失其中一端,即招来天怒人怨,也为国法所不容。另一方面对于法律与民众的现实关系,强调要广为教谕,使之周知易晓,反对不教而诛。但通观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法律体系越是完备复杂,越是远离百姓的视野。在获得法网“密而不漏”的好处同时,民间法律事务不得不求助于诸如“讼师”之类的非法的“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化的前提正是法律体系在日益复杂繁密之时,却远离了民众。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乐意看到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者来分享法律资源和尊严权势,因而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封建统治者总是想一相情愿地开展一项十分有趣的教化工作,把日益丰富的法律内容压缩成更简单的生活和处事规则,使老百姓耳熟能详,而漠视日渐复杂的财产关系正促使人们不断增强捍卫财产权利的意识。尤其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如何让老百姓熟悉和接受日益庞大复杂的律例体系,而又尽量减少甚至消除“讼师”对民间法律事务的非法干预,加大法律宣传与教育力度势在必行。通过接触丰富的历史材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无论政府和民间,在传播法律知识和开展法律教育方面,的确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花费了不少心血,做出了一些成绩: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br> 重视法律的宣传与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周礼。秋官。大司寇》中就讲到,每年“正月之吉”,大司徒、乡大夫要向民众悬法、颁法,其后州长、党正、族师每年分别向属民“读法”二、五、十二次,闾胥甚至每逢集会就向群众“读法”;经过儒家改造过的《周礼》当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我国自古以来由乡党什伍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却一直存在着集体教化、申明功过的传统,此即后来乡约保甲之祖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官府垄断法律知识和教育资源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人诠释法律并且讲学授徒的现象。“造竹刑”并教学生“执两可之说”的邓析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职业者”。据《吕氏春秋.离谓》所载,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在我国封建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看来,邓析也是教唆词讼的讼师鼻祖。但无论怎样评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他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显然是非常迫切的事情。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方针。法条成为教材,法吏成为楷模,不可谓不重视法律,但终因法令繁密、民无措手足而二世遂亡。秦汉之际,刘邦鉴于秦朝刑法“密如凝脂”,便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实际上就是以最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与老百姓当时最切近和最起码的法律要求。不仅如此,加强各级官吏学法用法,也是十分迫切的。三国魏明帝时,卫觊就曾认为“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并建议。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律博士之设反映政府已经开始把官僚学习法律知识摆到了议事日程。但到隋代,由于出现个别律博士玩法弄律,舞文作弊,隋文帝将律博士和部曹明法、州县律生一并停废。尽管当时人们不可能思考到道德风险问题,但从整个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阶层是否能忠实于法律和民众,已经开始受到怀疑。制定贴近民众的简洁明快的法律让更为广泛的人群学习掌握,不失为治道之先筹。律法简约是我国古代立法的基本要求,如被称为我国古代法典瑰宝的唐律就是以科条简约而闻名,其中已经蕴含着方便老百姓知法守法的深刻用意。<br> 明代朱元璋在阅览《律令直解》时,对大理寺卿周祯等人反复叮嘱:“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产晓。”“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洪武十九年五月,为申明游民之禁,“命户部板刻训辞,户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