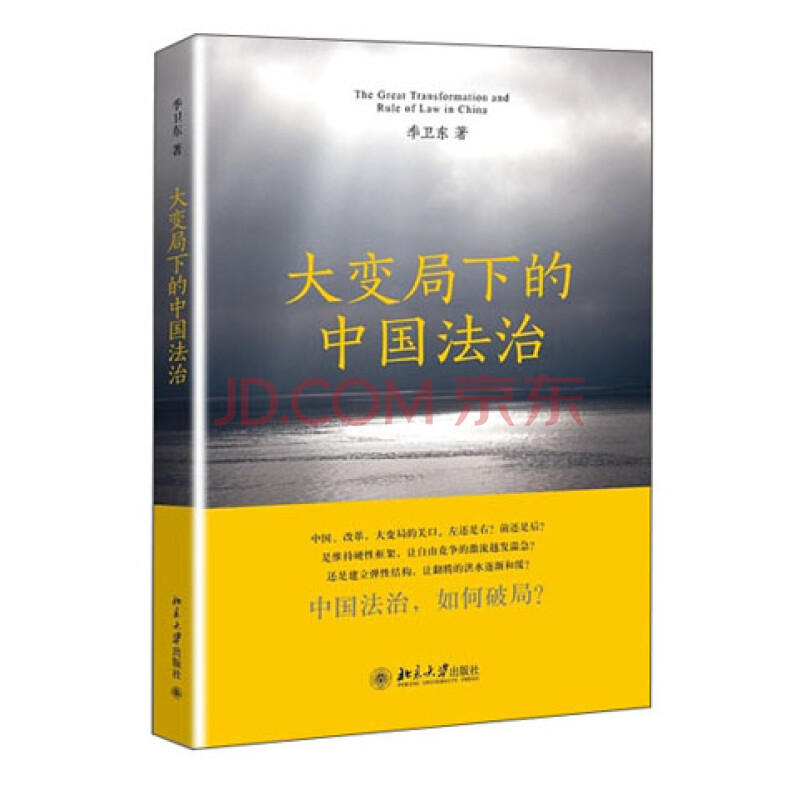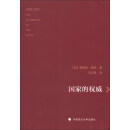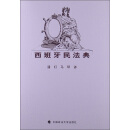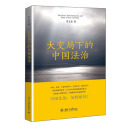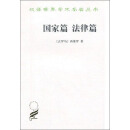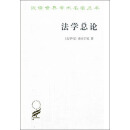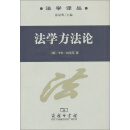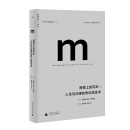内容简介
《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是季卫东教授多年来在国内知名报刊文章以及演讲记录的合集。全书围绕“大变局下的中国以及中国法治”而展开,由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始的法律记忆说起,围绕未来中国如何以最小化的代价进行改革这一命题层层展开。季卫东教授对中国的改革,不拆毁、不激进,冷静面对中国现实,所提方案深具建设性,是作者三十年来学术研究与对中国观察的精华所在。
精彩书摘
以最小化社会代价推动政治改革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可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刊登了两篇文章: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
谢韬的文章可谓新中国成立50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部门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
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1992年署名“皇甫平”,写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篇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1986―1987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由于之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除了这两篇党内非主流派的政论,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26日由新华社播发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1987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与法治――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蔓延、政府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理性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民主化这一点上,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20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等。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2007年曾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炎黄春秋》2007年4月号发表的、由陆定一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温总理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在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有可能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作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
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作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的障碍。财产申报制难以出台,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禁区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
目录
序
初始记忆
选择的自由与烦恼
法与时转则宜
十字路口
以最小化社会代价推动政治改革
大变局下中国法治的顶层设计
现代法治的精神
价值和制度的普遍性
和而不同
没有程序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可言
法制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
“程序共和国”宣言
决策的程序和语法
程序很重要,但不是万能药
通过互联网的协商与决策
法治突破
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与目标
司法改革第三波
中国司法改革第三波与法社会学研究
审判的推理与裁量权
日本司法改革与:民众参审的得失
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
法治原则与中国警务改革
时局万象
官员外逃的制度反思
爱国为何不守法
信访终结制与审判终局性
“祸从口出”的律师
“封口费”葫芦案
舆情的裂变与操纵
个人安全保障与宪政
如何面对一个风险社会
最高法院的使命与威信
期待地政拐点
“铁腕”执政功与过
人事与天命的碰撞
官员财产公示的“下行上效”
经济危机中的司法责任
法律:举起正义之剑
试读
以最小化社会代价推动政治改革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可作为判断的指标。
“一个法案”是指2007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逐步落实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化;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三篇政论文章”是指关于民主政治的三种不同主张及其互动关系。
《炎黄春秋》(2007年2月号)刊登了两篇文章: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
谢韬的文章可谓新中国成立50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当然,目前主要是批判,还没有看到赞同、拥护的意见。但通过批判促进讨论也很好,是正常的。政治应该容许理性讨论,让不同的意见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才能搞好政治。似乎有关部门目前仍然对这样的理性讨论持静观态度。
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周瑞金,是1992年署名“皇甫平”,写推动经济改革的著名系列文章的主要执笔人。他在这篇推动政治改革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政改的那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在1986―1987年期间,中共曾经缜密探讨过政治改革的问题。但由于之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断了将近20年。现在,这个空白正在被填补。
除了这两篇党内非主流派的政论,还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义。这就是党内主流派的表态定调,其标志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26日由新华社播发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是1987年提出来的,现在重新提起,很耐人寻味。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民主与法治――解决经济畸形发展、分配不公、腐败蔓延、政府信用度和执行力下降等问题。这篇文章,既是党内主流派对非主流派基于理想的民主化诉求的理性回应,也强调了中国现阶段民主化的特色和范围,试图说服激进化倾向,并试图使这种中国独自选择的民主化道路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体制的现状认识与发展方向展望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民主化这一点上,并没有对立之处。因此,可以把各种观点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和综合考察。
谢韬先生的文章重新评价了社会民主党的贡献,提出通过阶级和解和体制和解实现均富的路线诠释,要求把党的意识形态从阶级斗争转向阶级合作,转向社会协调,重新认识社会民主党。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20年前国内就有人开始研究,不过公开提出还是第一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等。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之间还存在本质的不同。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承认外部监督以及相应的议会政治。新华网2007年曾转载关于陆定一的回忆文章《炎黄春秋》2007年4月号发表的、由陆定一长子陆德整理的《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也提到“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借助外力”即党外监督的重要性。党内非主流派的文章,还明确提出重新认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主张。
至于党内主流派的立场,例如温家宝总理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样,已经开始把生产力发展与分配正义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不仅要继续把馅饼做大,而且还要重视把馅饼分好。温总理还在推动世界多极化,走中国独自的政治改革之路的前提下承认价值的普遍性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是在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刘熙瑞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发表文章,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新华网也转载了他的观点。按照我的理解,这既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渐进式政治改革路线的坚持,也暗示有可能已经作出关于政治改革的决断。一个问题不论多么艰难和歧义丛生,只有作出决断,才会有现实的存在,才能对现实进行改进。
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决断始终作不出来?为什么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的障碍。财产申报制难以出台,有些大案要案无法追查下去,就是很典型的实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禁区群众免费搭车的心理。
除此之外,专家在评估社会风险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也是妨碍政治改革决断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信息公开,在原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速度大幅度超出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摆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