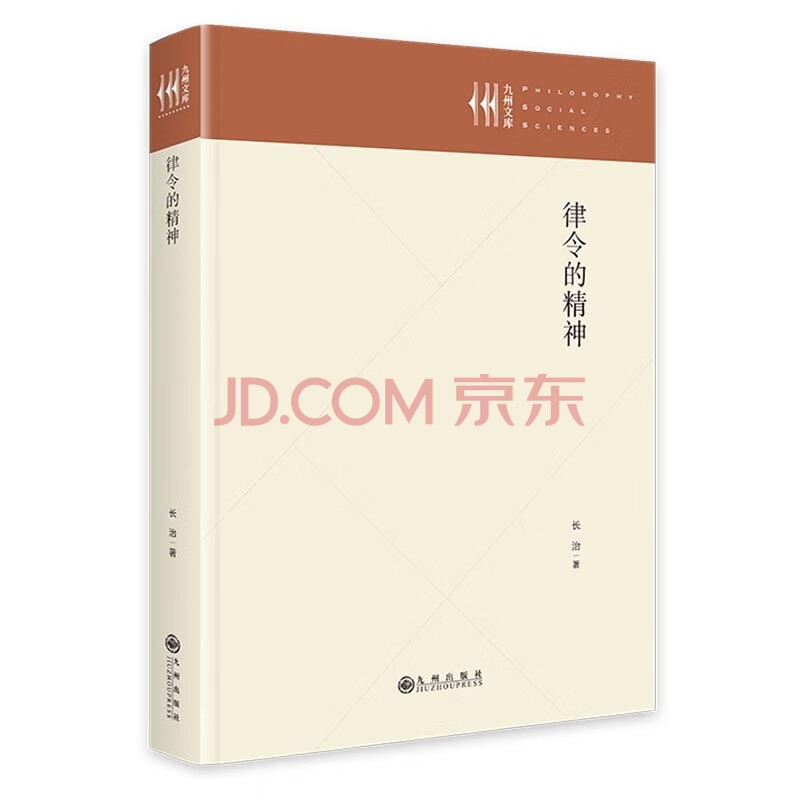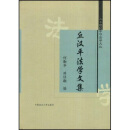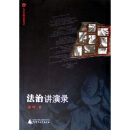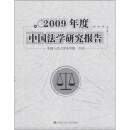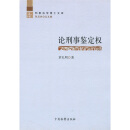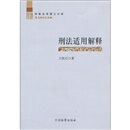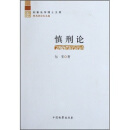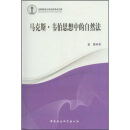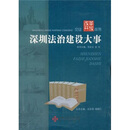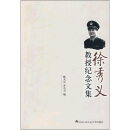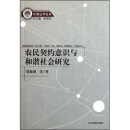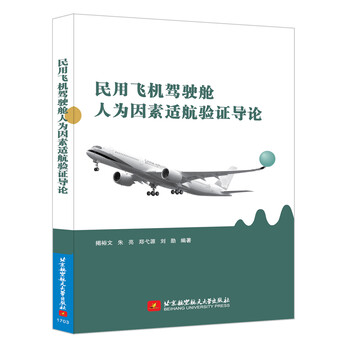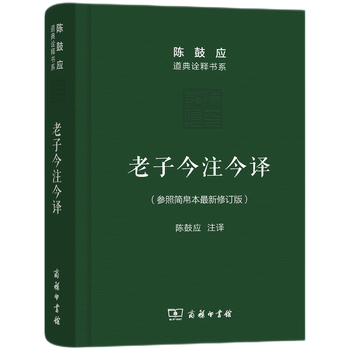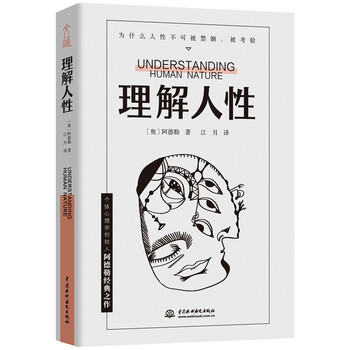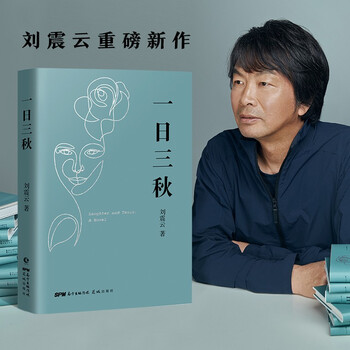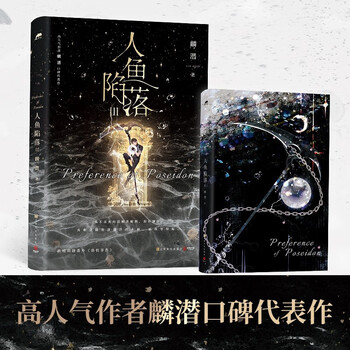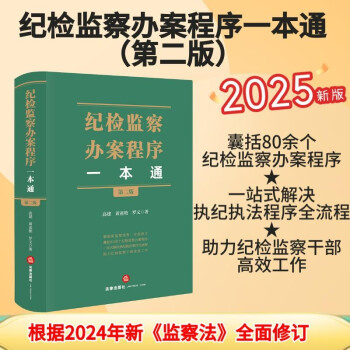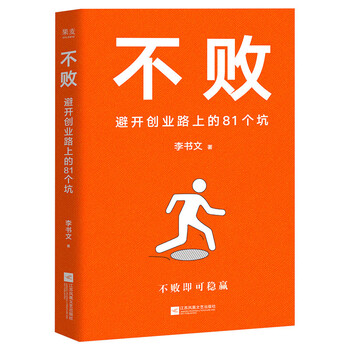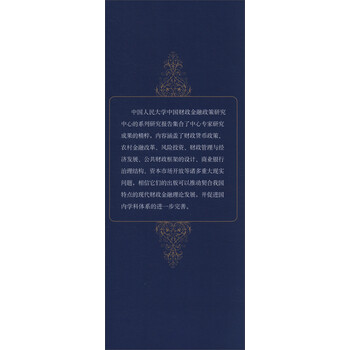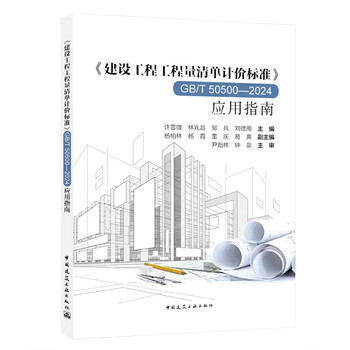内容简介
本书从法律形式及体系化现有法律的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律令两千多年演进史进行梳理,以经验材料为据,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由此发现:中国古代法是在单行法令充分发展、充分实施数百年,从而形成法的内容体系,并形成稳定的社会风俗、社会习惯之后,才开始制颁法律典籍(法籍)。法律形式的发展体现为从单行法令阶段向法籍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法籍阶段,仍不能忽视单行法令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仍需要通过发布新的或经修正的单行法令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完善。作为兼具法的内容体系与法的形式体系的法籍,是通过对之前颁行并仍然有效的单行法令进行汇合、整理而成的。对现有单行法令的整合、编纂而制成法籍的过程与方法,即法籍化,它与法典化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并无民法法系那样的法典化传统,而英美法系有类似于中国古代律令法籍化传统那样的法律整合传统。中国的律令传统有其不容否认的真理性和现代性,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根据主要研究对象,本书又可名为《中国古代法律方法,法籍论,兼驳法典论》。
目录
本书从法律形式及体系化现有法律的方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律令两千多年演进史进行梳理,以经验材料为据,考察其发生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由此发现:中国古代法是在单行法令充分发展、充分实施数百年,从而形成法的内容体系,并形成稳定的社会风俗、社会习惯之后,才开始制颁法律典籍(法籍)。法律形式的发展体现为从单行法令阶段向法籍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法籍阶段,仍不能忽视单行法令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仍需要通过发布新的或经修正的单行法令来推动法律的进步与完善。作为兼具法的内容体系与法的形式体系的法籍,是通过对之前颁行并仍然有效的单行法令进行汇合、整理而成的。对现有单行法令的整合、编纂而制成法籍的过程与方法,即法籍化,它与法典化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并无民法法系那样的法典化传统,而英美法系有类似于中国古代律令法籍化传统那样的法律整合传统。中国的律令传统有其不容否认的真理性和现代性,理应得到传承和发展。根据主要研究对象,本书又可名为《中国古代法律方法,法籍论,兼驳法典论》。
试读
第一章律令的起源初考
古代法中的律、令这二者的关键是“律”,因为“令”其实是古已有之且非始终存在。“律”是我国律令传统或古代法的特征与标志,且自秦至清都存在“律”这一法律形式。故,分析律令传统须以“律”为主要线索。
并且,对古代法的研究只能从“秦律”谈起,因为它是目前可知的、公认的律令传统源头,如下将从这个线索着手探究。但是,由于存在“法经”“改法为律”及“舜始造律”等极具混淆性的措辞,为正本清源,对这些问题也将在本章加以探究。
第一节“《秦律》”与“《汉律》”考
目前,学者们在论及秦朝的法律时,总是会言及秦朝有“《秦律》”(注意:这里是带书名号的,带书名号即意味着存在这一文件或图书)及汉朝有“《法律》”(也带有书名号),而且这样的说法因袭长久而几成定论。确实如此吗?
“秦律”与“《秦律》”之别,并不仅仅是有无书名号的问题,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在于使用或承认“《秦律》”这一表达即意味着承认秦朝时已经实现法律的编纂成书。那么,“《秦律》”这一表达的正确与否的关键是秦朝时有没有实现法律的编纂成书。如果没有编纂成书,则这一表达就是错误的。如果已经编纂成书,则这一表达就是正确的。则,只有查明史实才能辨明正误。
一、秦朝是否有《秦律》
为了解史实,我们将查阅古文献以进行考证。由于《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则我们以其为据进行考查,以求得可信之结果。以“秦律”为线索查找四库全书,去除重复的,共得到了十四条记录,其中出自唐人的有一条,出自宋朝人的有七条,出自宋朝以后的有六条:
草创之初,大臣无学,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图书,固难责以先王之制度也。
除挟书律。解题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秦亡,此禁虽弛,然犹载于律,至是始除之。
五月除诽谤妖言律。解题曰:“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然,则秦律也。颜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
秦律,敢有挟书者族。高帝不好诗书,尚仍秦旧。伏生之书藏而未出,浮丘之诗私相传习,高堂之礼、窦公制氏之桑皆湮欎未发。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况叔孙通降汉时有弟子百余人。项羽之亡鲁,为守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
汉高祖入秦,萧何收秦律令图书,汉王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强弱处,以何收图书也
及汉萧何得秦律令。
师古曰:“非也。若律历废则当径谓之‘十月’,不应有‘后九月’,盖秦律法置闰总于岁末,据汉书表及史记,汉未改秦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屡书“后九月”,是知故然,非历废也。”
盖收秦律令图书、举韩信、镇抚关中三者,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
汉高皇贱时,常就生民间饮王媪武负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群臣皆倚生晏,见上至甘,争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无故饮生者罚金四锾。文帝时始赐生于民酺三日。
秦律乍除闻板荡,孔墙中坏得肜戡。
汉章虽约法,秦律已除名。谤远人多惑,官微不自明。霜风先独树,瘴雨失荒城。畴昔长沙事,三年召贾生。
秦律,挟书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孝公初为赋,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改周制也。今其分寸不可考,汉大率依秦律历志所书。秬黍之法乃是王莽时刘歆之说。王应麟曰:皇祐新乐序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度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有四条是说汉相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之事,此事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也算是言之有据,但它只能说明秦朝确实有律、令、图、书,并不能说明秦朝有一部名为《秦律》的法律。况且,《史记》的原文是“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而后世引用的文字则变成了“收秦律令图书”,这显然是为了阅读便利而进行了改动。有两条是关于律历的,说明秦朝对音律、历法已有国家标准,所用的是“秦律法”“秦律历志”这样的措辞,同样不能说明秦朝有一部名为《秦律》的法律。其他的七条,两条出于古诗则不足为证,三条讲“挟书者族”,一条讲“诽谤妖言律”,一条讲“三人以上无故饮生者罚金四锾”。实际上,这十四条记载之中,只有三条涉及具体的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