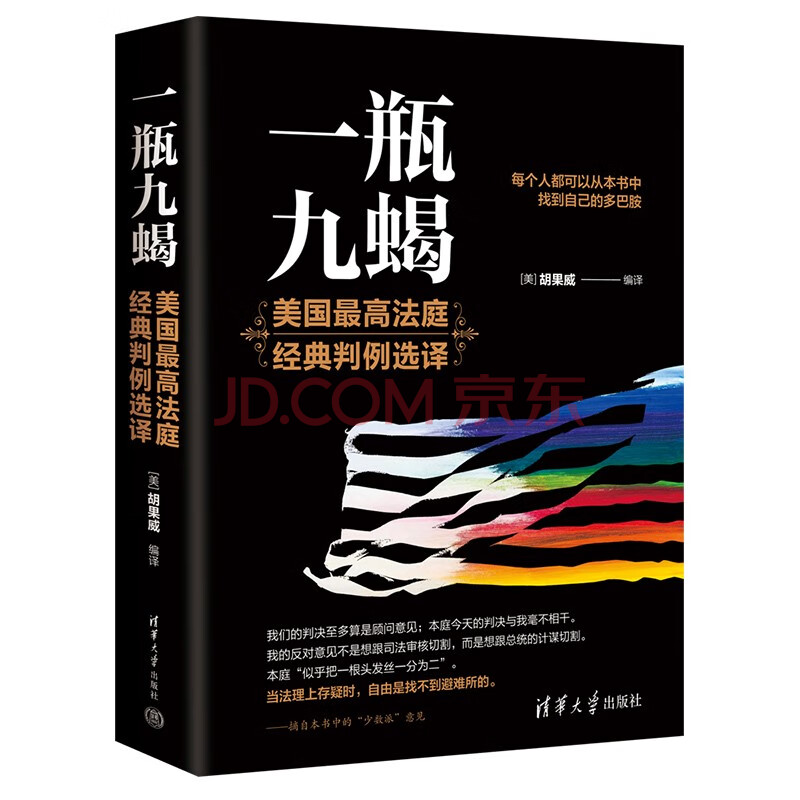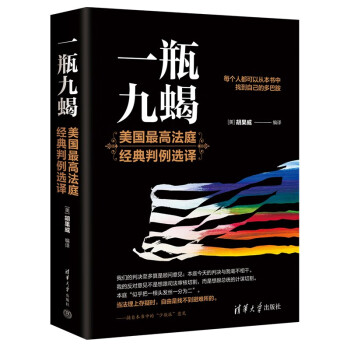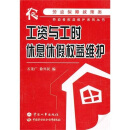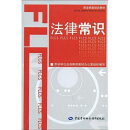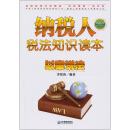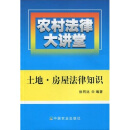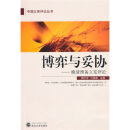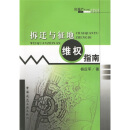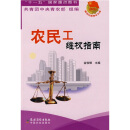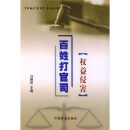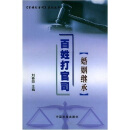内容简介
由九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庭被形容为“一个瓶子里装了九只蝎子”,他们仅对宪法和法律负责,是独立和平等的个体。司法决策的过程发生在复杂的制度环境内:是否签发调案令、如何就案件进行表决、由谁起草判决……凡此种种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和程序,九位大法官也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复杂的策略互动。
简言之,九只蝎子装在一只瓶子里,彼此间相爱相杀。
本书收录的大多是极具争议的案例,这些案例的判决并非黑白分明,往往是在见仁见智的灰色地带。
上诉到最高法庭的案子,除了多数派的判决之外,少数派的大法官们也会发表反对意见。一般的案例简介很少提及反对意见,多数派的判决也只能算是一面之词,如果只读多数派判决的简介而错过了少数派的反对意见,就相当于只看到了硬币的一面,无异少了半壁江山。
只有逐字逐句读了完整的判决才能体会到,反对意见往往也同样精彩,有时甚至比多数派的意见更精彩。
目录
第一章 美国宪法的起源和演变 1
第二章 联邦主义 8
马贝瑞诉麦迪逊 11
第三章 种族歧视 27
益和诉霍普金斯 31
普莱西诉弗尔格森 37
是松丰三郎诉美国 49
摩根诉弗吉尼亚 62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 66
贡米林诉莱特福特 70
洛文诉弗吉尼亚 75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评议员诉巴契 80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校长及校董案 129
巴特森诉肯塔基 145
第四章 言论自由 147
尼尔诉明尼苏达 152
《纽约时报》诉萨利文 167
廷克诉德莫因独立学区 182
科恩诉加利福尼亚 191
《纽约时报》诉美国 196
杨诉美国小型电影院公司 214
得克萨斯诉约翰逊 228
第五章 生命的权利 245
柔诉韦德 249
道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 269
克鲁赞诉密苏里卫生部长 274
伐蔻诉奎尔 307
第六章 性别和性取向歧视 312
菲利普斯诉马丁·玛丽埃塔公司 316
佛龙提埃罗诉理查德森 318
劳伦斯诉得克萨斯 322
美国诉温莎 341
欧泊吉费尔诉豪吉斯 370
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民权委员会 374
第七章 刑事被告的权利 399
若钦诉加利福尼亚 408
马普诉俄亥俄 414
罗宾逊诉加利福尼亚 430
季迪安诉温赖特 442
布瑞迪诉马里兰 449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 454
泰瑞诉俄亥俄 490
库里奇诉新罕布什尔 502
布鲁尔诉威廉姆斯 533
杰克布森诉美国 553
巴克卢诉普利赛斯 562
附录 《美国宪法》中英文对照 583
前言/序言
“一瓶九蝎”出自美国著名大法官小奥利佛·文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之口,他把由九位大法官组成的美国最高法庭形容为“一个瓶子里装了九只蝎子”。原则上这九位大法官仅对宪法和法律负责,在进行司法裁判时是独立和平等的个体。他们个人虽然是独立的,但司法决策的过程却发生在一种复杂的制度环境内。是否签发调案令、如何就案件进行表决、由谁起草代表法院的多数意见……凡此种种都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和程序,九位大法官也在这种制度环境内展开复杂的策略互动。简言之,九只蝎子装在一只瓶子里,彼此间相爱相杀,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霍姆斯大法官是提倡《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的先驱,他在1919年的西奈克诉美国案(Schenck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中有一句名言:“言论自由不保护在剧院里虚假地高呼失火而导致恐慌的人。”
至于为什么要全文翻译这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的经典案例,有两个前提需要解释:什么是经典案例;为什么要全文翻译,而不是摘要地介绍。
首先,本书收纳的这些案例大多是极具争议的案例,其中许多又是以5∶4 的微弱多数判决的案例,所以这些案例的判决并非黑白分明,往往是在见仁见智的灰色地带。例如1896年禁止具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旅客跟白人乘坐同一节车厢的普莱西诉弗尔格森案(Plessy v. Fergson),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日本裔美国公民和侨民送进集中营的松丰三郎诉美国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等,在后来的判例中又被推翻。本书之所以收纳这些案例,是因为这些案例非但揭露了美国司法的黑暗和不公,还能揭露有些虚伪的最高法庭大法官如何通过狡辩来混淆是非。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庭成立后的235年中,它共推翻了282件自己判决的案例,平均每年不止一件。但令人困惑的是,有些当年被推翻的案件,后来又被最高法庭翻案,这就不是“改邪归正”,而是“改正归邪”了。例如,1973年判决的柔诉韦德案(Roe v. Wade)推翻了若干个禁止妇女自主决定生育权的案例,确认了妇女人工流产的权利,当时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案例。然而因为特朗普总统在任上提名任命了3位保守的共和党大法官,形成了共和党大法官和民主党大法官6∶3的局面。2022年,尽管特朗普已经卸任,柔案又被道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这种左右摇摆的判断说明,美国的司法并不是独立和中立的,而是受政党和政治控制的,真可谓“错作对来对亦错,非为是处是还非”。
其次,美国最高法庭的案例通常很长,几十页的案例并不罕见,有的甚至一百多页,读起来很费时间和精力,所以几乎所有介绍美国最高法庭案例的著作都是摘要地简介。我为什么选译一些案例的全文,而不是摘要地翻译介绍呢?这就要从我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谈起。
我于1983年到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学院的学生有6门必修课,其余的是选修课。突然有了选课的自由,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选,加之还没有决定专业方向,于是第一学期便选了4门必修课,其中有一门是国际法。
国际法的老师是路易·翰肯(Louis Henkin),他是全世界国际法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编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通常都由某个院系聘请,如商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物理系或数学系等。但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位“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一位是翰肯教授,另一位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他们二位不是法学院和物理系聘的,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直接下的聘书,那是学校里最高的殊荣。
还记得上第一堂课,翰肯教授走上讲台就提了一个问题:“在离美国200海里的公海上有一艘不明国籍的船,船上有一台印刷机正在印美钞。你是美国总统的法律顾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办?”然后,他看着讲台上的名单随便叫了一个同学,那位同学毫无准备,支支吾吾地不得要领。有些同学急了便纷纷举手,争着为总统出谋献策;另一些同学则提出反对意见,课堂马上就活跃起来。翰肯教授从来不照本宣科地讲课,只是偶尔提一两个问题,把学生带进下一场辩论,他在旁边引导辩论的方向。这就是美国法学院普遍采用的“苏格拉底教学法”(Socratic method)。
上翰肯的课负担很轻,平时既没有作业,期中也没有考试,而且期末还是开卷考。还记得最后那道占总分二分之一的写作题:“美国政府收到古巴政府的照会,要求美国归还关塔那摩湾的军事基地。如果你是美国总统的法律顾问,你认为美国该怎么办?”关塔那摩湾本来是古巴领土,在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中被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走。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凡是被强权霸占的领土,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理应归还。但转念一想,我是总统的法律顾问,如果我建议美国把关塔那摩还给古巴,那不是吃里扒外吗?于是,我翻了半天书,但还是找不到任何不归还的理由,反而找到了若干条应该归还的理由。犹豫再三,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