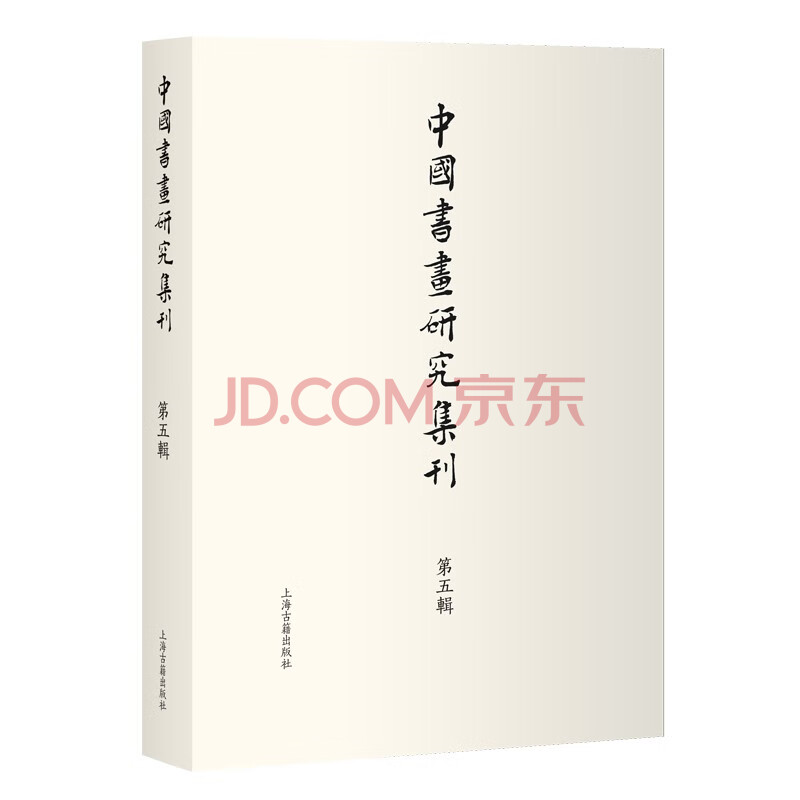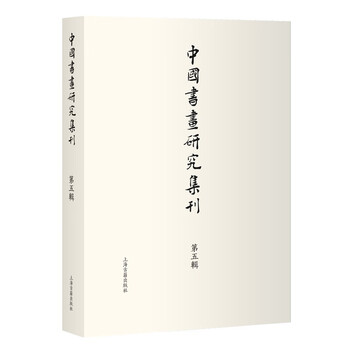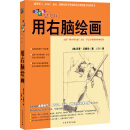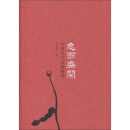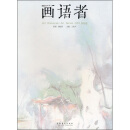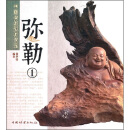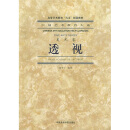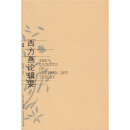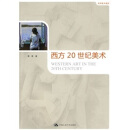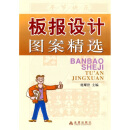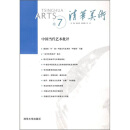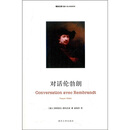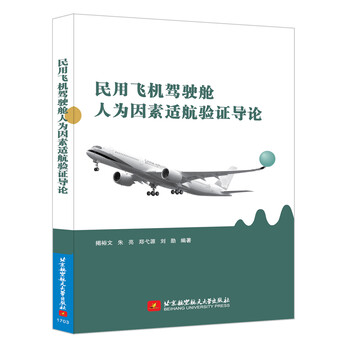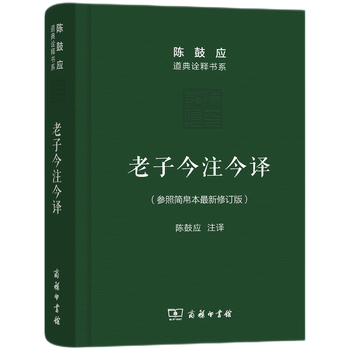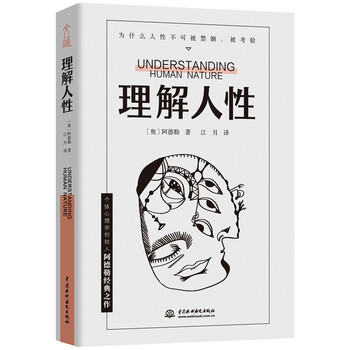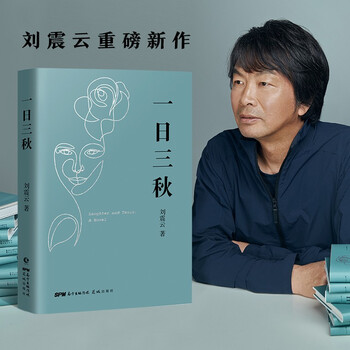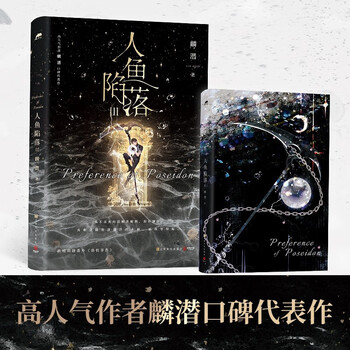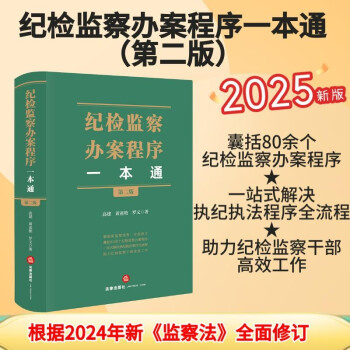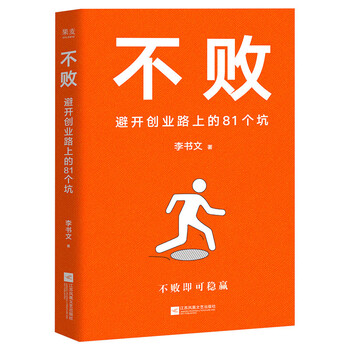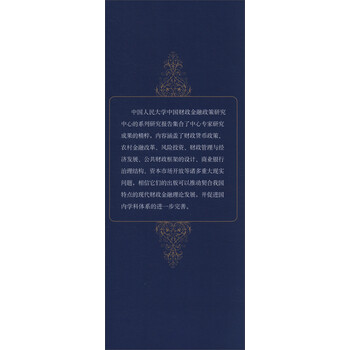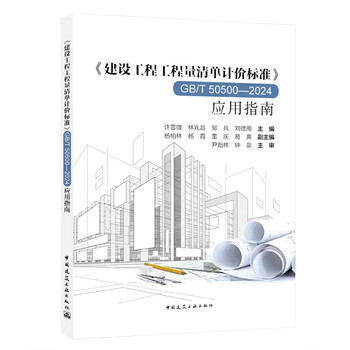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中国书画研究集刊》主要刊载与中国书画研究有关的文章,每半年一辑,16开,繁体横排,配以彩色图版,所刊文章文体、长短、中英文均不设限,常设栏目包括论文、学术札记(文献笺注、史料钩沉与考释、研究综述等)、书评等。集刊的出版,旨在为海内外高质量的中国书画研究成果提供发表与交流的平台,推进本领域研究不断深化。
本辑为第五辑,收录了石守谦、黄书梅、吴嘉龙、林俊臣、温安俊、王家葵、薛龙春、陈博洋等人的学术论文或考释札记共8篇,内容包括从沈周“日常即兴”画意谈吴门艺术的历史意义,清初印画关系初探,《江村销夏录》一书的流传与阅读,从身体思维的角度重审碑学与帖学的经典化问题,“西域三汉刻”的命运,王羲之法帖中三个话题的考证,新见黄易友朋往来书札的考释,读《张好好诗卷》札记五则,等等。另外还有陈硕、陈波帆的书评与综述各一篇,分别就托马斯·凯利《器用与铭文》一书、中国书法与身体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
目录
史論
吴門藝術的歷史意義——從沈周“日常即興”的畫意談起/石守謙
Seal-Painting Relationship in the Early Qing: A Case Study on Gong Xian’s Met Albums/Amy S. Huang
論《江村銷夏録》之流傳與閲讀/吴嘉龍
書法的經典問題諏議:身體思維下的碑學與帖學/林俊臣
“西域三漢刻”的命運/溫安俊
考證
右軍帖三題/王家葵
新見黃易友朋往來書札考釋/薛龍春
札記
讀《張好好詩卷》札記五則/陳博洋
書評與綜述
金石不朽乎?——托馬斯斯凱利著《器用的銘文:早期近代中國的書寫與物質性》跋/陳 碩
中國書法與身體研究述略/陳波帆
《中國書畫研究集刊》稿約及格式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