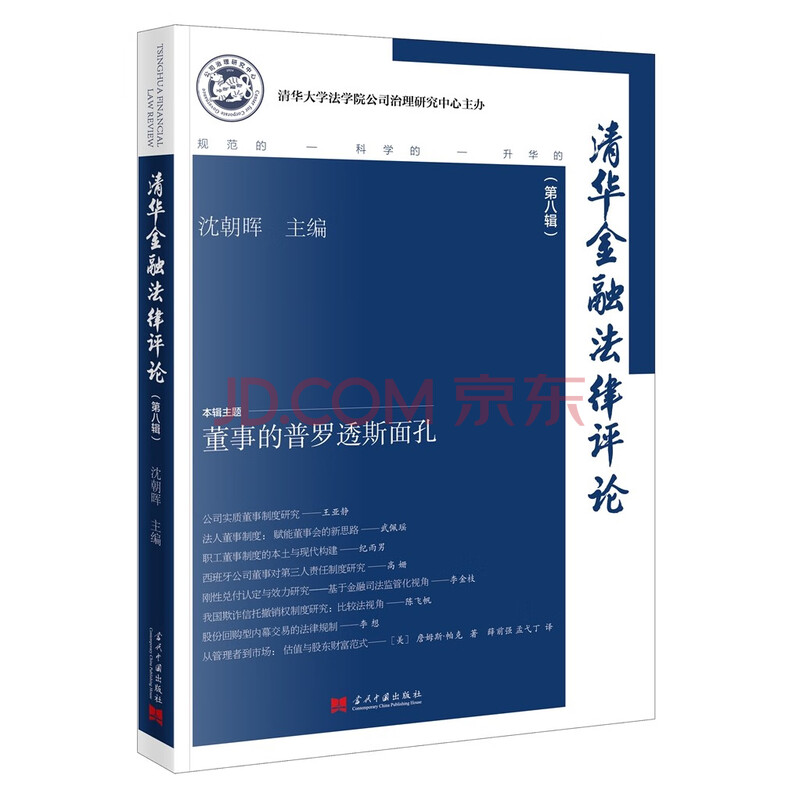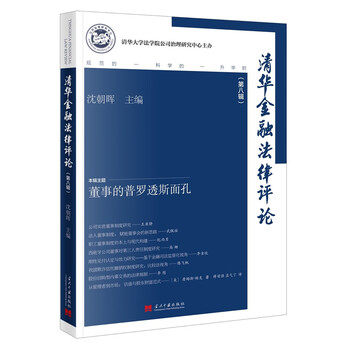内容简介
修订的公司法于2023年12月颁布,并于2024年7月正式开始施行,最新法新规的解释、实施和未来走向,不仅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投资者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也有互动的深远价值。本辑以“董事的普罗透斯面孔”为主体,共收录了8篇文章,分别对公司法人董事制度、如何赋能董事会、公司董事与第三人责任、信托模式资产管理、刚性兑付的认定与效力、欺诈信托撤销权制度、股份回购的内幕交易法律规制以及职工董事制度的构建等进行了探讨。
精彩书摘
公司实质董事制度研究王亚静
摘 要:“影子董事”“事实董事”作为英美法系的舶来概念,与我国公司法语境下的概念——“实际控制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皆能够起到规制不正当干涉公司事务行为的作用,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均有不同。我国虽设有实际控制人条款及禁止股东权利滥用的一般规则,却在对控制权的规制上具有一定的局限。实际控制人条款的规制基点在于支配公司而非影响董事,规制主体未能涵盖所有能够指使董事或实际行使董事职权之人,规制行为范畴不够周延,在责任承担方面对实际控制人义务性质认识的不明晰使得责任追究存在实操上的难度。结合域外立法经验可知,实质董事的理论基点在于“关键资源理论”;在责任性质及范围方面,尚存在完善空间。
关键词:影子董事;事实董事;实际控制人
一、问题的提出
在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公司法并未对股东因涉足公司管理运营而应承担的责任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股份集中度相对较低的公众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决策通常较难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法律往往不会对此施加特殊的规制。然而在实践中,管理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模式产生变化,作为非经营管理人员的股东或其他对公司具有控制力之人逐渐介入公司经营和管理决策。《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作为名词的“控制”如此解释:通过持有具备表决权的证券、合同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个体或团体的管理和政策的权力。公司控制权一般是指对公司所具有的实质性控制力和影响力,往往是基于财产权和内部权力分配规则等因素产生。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指出,公司制度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财富得以累积、壮大,由此造成了极少数人掌握控制权的结果。掌握权力的群体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控制:一是通过法律赋予其的权利获得董事选举权;二是直接施压于董事,对其决策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动用选举董事的权利往往并不是这种控制权实现的方式,更常见的方式是直接或间接地对董事给予指令。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因而公司的所有者与控制权人也并非对应关系。公司控制权人将可能通过实质参与公司管理而享有经营权,但因法律规定的缺失,其可以避免承担董事义务,这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偏离立法初衷。以我国公众公司为例,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公司“董事席位瓜分”已成为普遍现象,即股东普遍以协议等方式拥有安排董事会席位的权利以实现委派董事、控制董事会成员席位的目的。
为对享有公司控制权且实质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经营但法律未加以限制的主体进行规制,各国及地区均积极探索立法规范。典型代表如英国,其确立的实质董事的立法模式,即引入了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之概念,将董事义务落脚于事实上行使了董事职责或操控董事行为的主体。与之类似,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我国台湾地区等也采取了类似于实质董事的进路。一直以来,我国《公司法》坚持奉行“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模式,根据2023年《公司法》第59条及第178条第2款,董事须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不承认未经过法定程序选任产生的董事。为解决前述问题,我国《公司法》设置了“实际控制人”,虽然能够通过不同路径在部分情形下实现与实质董事相同的效果,但与影子董事、事实董事等实质董事之间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偏向与规制路径差异。
2023年《公司法》中新增的第192条表明我国《公司法》计划引入实质董事认定的理念。本文认为,《公司法》第192条是对我国公司法语境下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责任的完善,借鉴了英国法的“影子董事”理念,但在引入实质董事制度层面仍不够成熟。本文将结合我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规制现状对域外相关立法规范作出深入研究,对我国《公司法》通过实质董事路径规制实质影响董事决策的不当行为提出思考与建议,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制控制权人的条款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
[专题一]董事的普罗透斯面孔
公司实质董事制度研究 王亚静 /
法人董事制度:赋能董事会的新思路 武佩瑶 /
职工董事制度的本土与现代构建 纪雨男 /
西班牙公司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研究 高 姗 /
[专题二]信托与资管
刚性兑付认定与效力研究
——基于金融司法监管化视角 李金枝 /
我国欺诈信托撤销权制度研究:比较法视角 陈飞帆 /
[专题三]证券市场与法治
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 李 想 /
从管理者到市场:估值与股东财富范式 [美]詹姆斯·帕克 著 薛前强 孟弋丁 译 /
试读
公司实质董事制度研究王亚静
摘 要:“影子董事”“事实董事”作为英美法系的舶来概念,与我国公司法语境下的概念——“实际控制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皆能够起到规制不正当干涉公司事务行为的作用,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均有不同。我国虽设有实际控制人条款及禁止股东权利滥用的一般规则,却在对控制权的规制上具有一定的局限。实际控制人条款的规制基点在于支配公司而非影响董事,规制主体未能涵盖所有能够指使董事或实际行使董事职权之人,规制行为范畴不够周延,在责任承担方面对实际控制人义务性质认识的不明晰使得责任追究存在实操上的难度。结合域外立法经验可知,实质董事的理论基点在于“关键资源理论”;在责任性质及范围方面,尚存在完善空间。
关键词:影子董事;事实董事;实际控制人
一、问题的提出
在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公司法并未对股东因涉足公司管理运营而应承担的责任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股份集中度相对较低的公众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决策通常较难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法律往往不会对此施加特殊的规制。然而在实践中,管理权和所有权相互分离的模式产生变化,作为非经营管理人员的股东或其他对公司具有控制力之人逐渐介入公司经营和管理决策。《布莱克法律词典》对作为名词的“控制”如此解释:通过持有具备表决权的证券、合同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个体或团体的管理和政策的权力。公司控制权一般是指对公司所具有的实质性控制力和影响力,往往是基于财产权和内部权力分配规则等因素产生。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指出,公司制度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财富得以累积、壮大,由此造成了极少数人掌握控制权的结果。掌握权力的群体往往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控制:一是通过法律赋予其的权利获得董事选举权;二是直接施压于董事,对其决策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动用选举董事的权利往往并不是这种控制权实现的方式,更常见的方式是直接或间接地对董事给予指令。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因而公司的所有者与控制权人也并非对应关系。公司控制权人将可能通过实质参与公司管理而享有经营权,但因法律规定的缺失,其可以避免承担董事义务,这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偏离立法初衷。以我国公众公司为例,数据显示,我国公众公司“董事席位瓜分”已成为普遍现象,即股东普遍以协议等方式拥有安排董事会席位的权利以实现委派董事、控制董事会成员席位的目的。
为对享有公司控制权且实质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经营但法律未加以限制的主体进行规制,各国及地区均积极探索立法规范。典型代表如英国,其确立的实质董事的立法模式,即引入了事实董事与影子董事之概念,将董事义务落脚于事实上行使了董事职责或操控董事行为的主体。与之类似,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我国台湾地区等也采取了类似于实质董事的进路。一直以来,我国《公司法》坚持奉行“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模式,根据2023年《公司法》第59条及第178条第2款,董事须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不承认未经过法定程序选任产生的董事。为解决前述问题,我国《公司法》设置了“实际控制人”,虽然能够通过不同路径在部分情形下实现与实质董事相同的效果,但与影子董事、事实董事等实质董事之间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偏向与规制路径差异。
2023年《公司法》中新增的第192条表明我国《公司法》计划引入实质董事认定的理念。本文认为,《公司法》第192条是对我国公司法语境下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责任的完善,借鉴了英国法的“影子董事”理念,但在引入实质董事制度层面仍不够成熟。本文将结合我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规制现状对域外相关立法规范作出深入研究,对我国《公司法》通过实质董事路径规制实质影响董事决策的不当行为提出思考与建议,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国《公司法》有关规制控制权人的条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