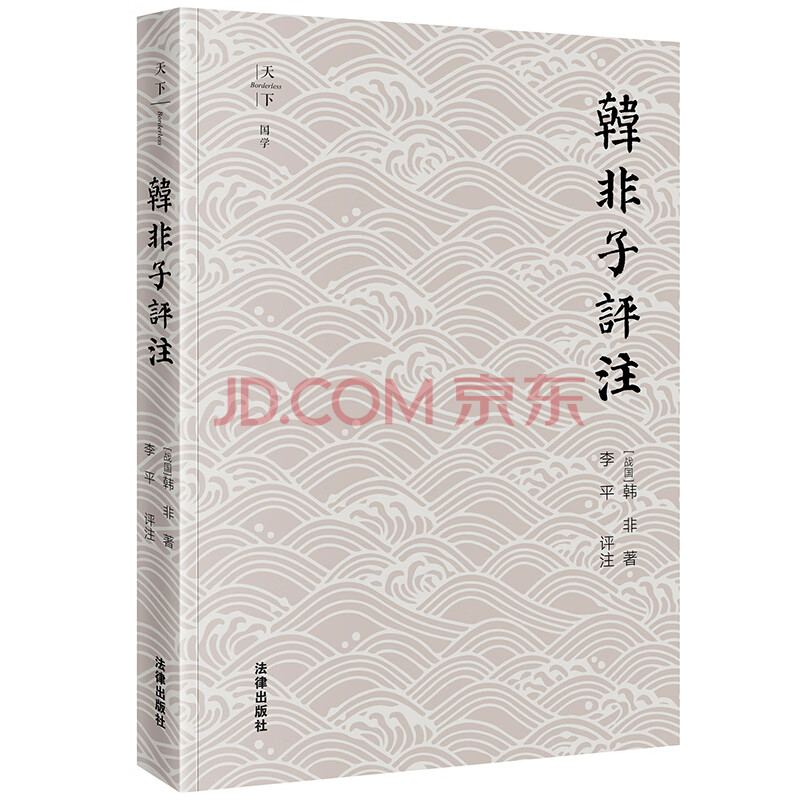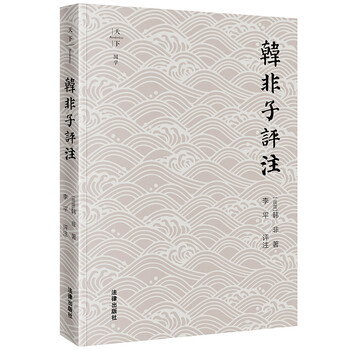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关于韩非和《韩非子》的论著极多,几乎涵盖了注、译、述、论等所有模式。不过其中问题仍旧不少:倾向于历史还原者,往往失之俗;精于考据校雠者,每每失之浅;长于义理阐发者,常常失之真;急于古为今用者,难免失之浮;以特定学科视角介入者,又不免失之偏。因此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准确全面地呈现韩非的思想,平易近人的同时又具有义理深度和理论价值,是着实不易的。而返回经典本身,始终是准确把握韩非思想的可靠方案,也是校验各种阐发是否言之成理的可靠途径。本书尝试将《韩非子》作为韩非的思想总集,带入战国中晚期的政治社会情景和思想环境中,围绕韩非的问题、困境和所作出的理论创化,对《韩非子》文本作出尽可能准确和有深度的评注。
目录
目 录
凡 例
绪 说
初见秦第一
存韩第二
难言第三
爱臣第四
主道第五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扬权第八
八奸第九
十过第十
孤愤第十一
说难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奸劫弑臣第十四
亡征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备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饰邪第十九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一
说林上第二十二
说林下第二十三
观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体第二十九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难一第三十六
难二第三十七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难势第四十
问辩第四十一
问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说疑第四十四
诡使第四十五
六反第四十六
八说第四十七
八经第四十八
五蠹第四十九
显学第五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饬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附录1 《史记·韩非列传》
附录2 先秦两汉有关韩非的评论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绪 说
近代以后有关韩非和《韩非子》的论著极多,几乎涵盖了注、译、述、论等所有模式。用一句话来概括,可说是极尽研究者所能,做了全方位、多模式、多视角、多样化的研讨。借助这些成果,读者眼前的韩非越来越立体,也愈加淋漓尽致。不过其中的问题仍旧不少:倾向于做历史还原者,往往失之俗;精于考据校雠者,每每失之浅;长于义理阐发者,常常失之真;急于古为今用者,难免失之浮;以特定学科视角介入者,又不免失之偏颇。遑论近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西释中、反向格义之风大盛,径以西方学理、价值为标准遴选、品评乃至批判国故,至今积弊仍在。于是,对初入门径者而言,一个现代式的韩非似乎不难理解,却总难免失真;对研究者来说,通说共识多有不确,但不免发现越是深入精研,越难以“浅出”。因此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准确全面、去繁就简地呈现韩非的思想,平易近人的同时又具有义理深度和理论价值,对学者的功力和笔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而返回经典本身,对于学者而言始终是准确把握韩非思想的最可靠方案,也是校验各种阐发言之成理与否的最可靠途径。
人们阅读经典,诠解经典,总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期许。可是圣贤无不仰之弥高,如何能上得巨人肩头,又如何能将一己之见通过著述化成后学渐进于道理的公器,却是历代读书人共同面对的难题。至少早自战国便已形成解经的传统,例如《墨子》中保留的《经说》是对《墨经》的解释,《管子》中《版法解》句解《版法》篇,《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句解《老子》,另外还有《文子》全书几乎都可以看作为《老子》作解。西汉以后逐渐显学化的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解读之学,并且逐渐形成基于训诂的今文经学和基于古文字的古文经学两大传统,可分别以何休的《公羊解诂》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为代表。魏晋以后玄风大兴,寄玄理于经注,为经典注疏在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外另辟一径。此中王弼的《老子》《周易》注和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最为佳作。同时,汉传佛典的注释以及仿自“论”藏的经论、义论,为经典研究带来新的理论资源和论说范式,例如《大智度论》和《肇论》等。唐承隋制行科举取士,开明经一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官方定本,经学地位隆盛至极。但经典的义理阐发反受制于科考。诸子典籍注释诠解,除了与道教有渊源关系的《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外亦多被边缘化。宋明以后解经风格迎来一大转折,要者有二:一是理学家的“六经注我”模式兴起,二是大量融会儒释道三家理论资源。但对诸子经典的注疏阐发仍旧非常有限。随着金石学和受佛教影响迅速发展的版本、目录学日益成熟,考据、疑古之风渐盛。清人之学,功在校雠。这一点只需看清人校勘本典籍,如阮刻十三经注疏、新编诸子集成中清人注本在当下被当作善本引用的普遍性便可知悉。很多典籍有赖于清人反复考校方始可读,最典型者莫过于孤本存于《道藏》的《墨子》。可是清人多长于考据而疏于义理,虽后期今文经学和居士佛学略有改观,但仍不可与宋学同日而语。
总括来说,传统时代义理阐发多依赖经注模式,也不乏散文、语录式的专论。问题在于,注疏模式容易紧扣经典文本,但是给读者带来了很大难度:一是由于观点难以系统化表述,二是难以分辨何为原生,何为注家创化,例如《庄子》文本、郭象注和成玄英疏。而传统的专论往往又显得过于粗略,虽每有提纲挈领或画龙点睛之效,却难以提供全面细致的解说。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强势东渐,研究和著述的范式也随之变化,最突出者有三:一是“论文”式研究成果占据主导;二是西学成为新的理论资源,甚至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标准;三是著述形式渐趋多样化。冯友兰曾经区分研究哲学的两种方式,他称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以之为借鉴,古今依托经典阐发义理的作品,大抵可分如下模式:其一,“照着说”。我们首先来看两个例子,一是史家的“重述”。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史记·五帝本纪》中大篇幅重述《尚书》相关篇目的部分。二是传统经学有个说法叫作“疏不破注”,所以理论上最典型的“疏”理应是“照着说”的典范。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毫不夹杂“私货”的纯说明性“疏”并不存在。还有像多数“评传”“今注今译”类作品中的译注评述,这类作品的优劣前文已述。其二,“接着说”。其中又可分两大类型:一者以孟子之于孔子、子思,庄子之于老子为典型;二者可以王弼注《老子》,朱子注“四书”为例。这种模式既需要对原典有着极为精深的理解把握,又要求作者具有天才式的创化能力。对于人类智慧和哲理思考的推进而言,这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形式。不过这类作品对读者,尤其是尚未吃透原典的读者来说可谓极不友好。其三,“挑着说”。近代以来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专论、论文体例,就经典文本或思想中的某一个或一些问题展开专门且深入的论说。这更像是一种专家式的研究,或许针对特定领域、人群而言能够产生价值,但终究受制于过于专业化的“学术”规范和形式,难以获得广泛受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