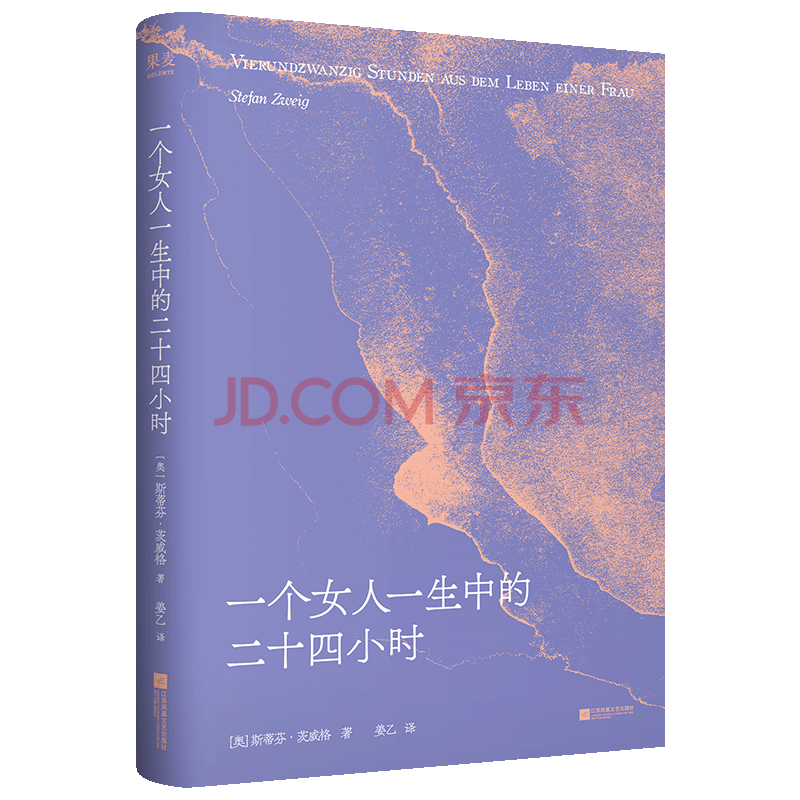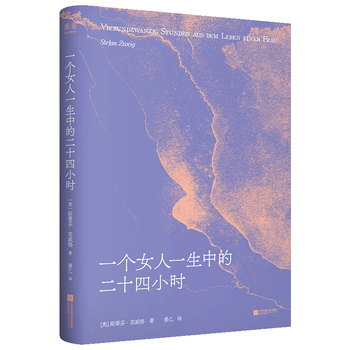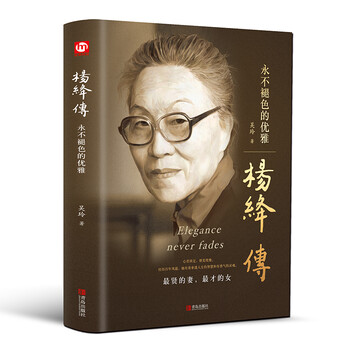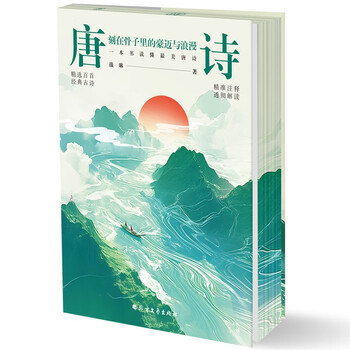内容简介
C夫人是一位满头银发、气度不凡的英国贵妇人。谁都无法想到,这位平时只是独自一人安静地读书、弹琴的老太太,她的内心却始终被一件陈年往事束缚着。
在四十二岁那年,C夫人独自一人逃离了空虚与压抑的生活。在蒙特卡洛的赌馆里,她遇到了一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输光了全部财产,正绝望地准备走向死亡。不知是出于某种崇高的感情,抑或是瞬间激情的驱使,C夫人试图拯救这个她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二十四小时里,她经历了疯狂的爱与惨痛的失去。这短短的二十四小时是她一生中少有的放纵,也引领她完成了直面自我的救赎。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奥地利知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撰写的中篇小说,也是一部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齐名的经典名篇。
精彩书评
1. 我一口气读了他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我每分钟的心跳在八十次到九十次之间,茨威格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激动,同时又没有生命危险。——余华
2. 关于《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我要补充一点:这个短篇您写得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比收进俄文版这两本书里的所有作品都更具匠心。——高尔基
精彩书摘
当时离大战爆发尚有十年,我下榻在里维埃拉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我们的餐桌上爆发了一场激烈讨论,不知不觉间,讨论竟变成粗暴的争执,甚至快到了相互谩骂和羞辱的地步。大多数人想象力匮乏,凡不直接触及他们,不能像尖楔般强行夯击他们感官的事件,他们一概无动于衷。可一旦事情发生在眼前,直接触动他们的情感,哪怕是小事一桩,也会立即激发他们超乎寻常的热情。某种程度上,平日里他们的漠然置之,会被一种不得体的、过火的激烈态度取代。
这次,在我们这个地道的市民气的晚餐桌上,情况正是如此。大家本来会在这种场合心平气和地闲聊,无伤大雅地开些小玩笑,吃完饭后通常立即四散而去:德国夫妇,热衷于摄影,会外出郊游拍照;稳重的丹麦人去忙着沉湎于无聊的钓鱼;高贵的英国夫人去看她的书;意大利夫妇去蒙特卡洛碰运气;而我则去花园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地躺着,或去工作。然而这次,我们彻底沦陷于这场痛苦的争论中,谁也不愿离席。要是我们中有人突然一跃而起,那绝不是像往常一样准备礼貌地起身告辞,而是在头脑发热的盛怒中――正如我方才所述――索性采取的近乎暴躁的态度。
然而让我们这一小桌人如此不快的事,确实足够离奇。我们七人借住的这家小旅馆,虽说外部看来是幢独栋别墅――哦,从窗户望出去,岩石嶙峋的海岸,景色多么迷人!――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皇宫大饭店的侧翼,收费较低廉,以花园与之相连,因此我们这些住在侧楼的人,与大饭店的客人常来常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发生了桩不折不扣的桃色事件。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乘午间列车到了饭店(我必须确切交代他到达的时间,因为时间对这桩绯闻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对激发我们热烈讨论的主题)。他要了间面朝大海的房间:这本身即可说明,此人景况颇为优渥。然而,令他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内敛的雅致,更是他非凡的、极具魅力的俊美:少女般的瘦长脸上,金色的短髭丝绸般抚摩着感性温柔的嘴唇,白皙的额上卷着柔软的波浪状棕发,柔情似水的双眸,每一瞥都像在给人爱抚――他气度温和、热切、和蔼可亲,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惺惺作态。如果说从远处看,他让人联想到大型时装店橱窗里代表男性美、手握精美手杖的玫瑰色蜡人,那么仔细一瞧,任何对他先入为主的纨绔印象均会消失,因为在他身上(极为罕见!),亲切动人与生俱来,就像从他皮肤里长出来的一样。他以同样谦逊诚恳的态度,问候每一个他路过的人。而观察他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地时刻准备展示他的优雅,实在令人赏心悦目。例如他会疾步上前,为某位走向衣帽间的女士提前拿取大衣,他会对每个孩子投以友善的目光,并说上几句俏皮话。他证明了自己既擅长交际,又细致入微――简言之,他一看就是个蒙福之人。这类人从久经考验的感觉中生出自信,深信他们能以潇洒的外表和青春魅力让他人感到愉悦,并将这份自信转化为全新的优雅。对于住在大饭店里,占绝大多数的年老多病的客人来说,他的临在,无疑是种祝福――他迈着青春的胜利步伐,裹挟着轻盈清新的生命之风,正如他的优雅像件礼物,奇妙地赠予一些人,他本人也不可抗拒地步入众人的心田,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来了才不过两小时,就和里昂来的心宽体胖的工厂主的女儿们――十二岁的安妮特和十三岁的布兰奇打起了网球,而她们的母亲,精致细腻、性格内向的亨丽埃特夫人,看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儿不经意间卖弄风情,与年轻的陌生人眉来眼去,脸上不禁露出轻柔的微笑。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局一小时,期间还悠闲地讲了些精彩的逸闻趣事,随后又陪亨丽埃特夫人,在她的丈夫像往常一样,和一位生意上的熟人玩多米诺骨牌时,去露台上长时间散步。深夜,我注意到他在办公室的暗影里,与大饭店的女秘书交谈,其态度之亲密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的丹麦同伴去钓鱼,同样显露出他在钓鱼方面的绝学,之后和里昂来的工厂主长谈了番政治,又证明了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至少,人们听见这位胖先生爽朗的笑声盖过了阵阵海浪的轰鸣。午饭后――我有必要为了说明情况,准确地交代他在各个阶段的时间分配――我又看见他和亨丽埃特夫人在花园里喝了一小时黑咖啡,和她的女儿们打了一次网球,还在大厅里和那对德国夫妇攀谈。下午六点钟,我去寄信,在火车站遇见他。他急匆匆朝我走来,像是非道歉不可似的跟我说,有人突然叫他回去,但两天后他会再回来。晚饭时,他确实没有出现在餐厅,但这不过是见不着他的身影而已,因为各个餐桌上的人们都在议论他,大伙儿都在纷纷夸赞他轻松乐观的生活态度。
夜里,大概将近十一点,我正坐在房里,想把一本书看完。突然,透过敞开的窗户,我听见花园里不安的叫喊声,大饭店那边显然嘈杂一片。与其说好奇,不如说惊慌,我立即奔到了距离侧楼五十步路的大饭店,发现客人和职工惊慌失措,已然乱作一团。原来亨丽埃特夫人,在她丈夫通常与他来自慕尔的朋友们玩多米诺骨牌的时间去海滨露台散步,此刻却一直未归,于是大家担心她遭遇不测。她那平时气
试读
当时离大战爆发尚有十年,我下榻在里维埃拉的一家小旅馆里。那天,我们的餐桌上爆发了一场激烈讨论,不知不觉间,讨论竟变成粗暴的争执,甚至快到了相互谩骂和羞辱的地步。大多数人想象力匮乏,凡不直接触及他们,不能像尖楔般强行夯击他们感官的事件,他们一概无动于衷。可一旦事情发生在眼前,直接触动他们的情感,哪怕是小事一桩,也会立即激发他们超乎寻常的热情。某种程度上,平日里他们的漠然置之,会被一种不得体的、过火的激烈态度取代。
这次,在我们这个地道的市民气的晚餐桌上,情况正是如此。大家本来会在这种场合心平气和地闲聊,无伤大雅地开些小玩笑,吃完饭后通常立即四散而去:德国夫妇,热衷于摄影,会外出郊游拍照;稳重的丹麦人去忙着沉湎于无聊的钓鱼;高贵的英国夫人去看她的书;意大利夫妇去蒙特卡洛碰运气;而我则去花园的椅子上无所事事地躺着,或去工作。然而这次,我们彻底沦陷于这场痛苦的争论中,谁也不愿离席。要是我们中有人突然一跃而起,那绝不是像往常一样准备礼貌地起身告辞,而是在头脑发热的盛怒中――正如我方才所述――索性采取的近乎暴躁的态度。
然而让我们这一小桌人如此不快的事,确实足够离奇。我们七人借住的这家小旅馆,虽说外部看来是幢独栋别墅――哦,从窗户望出去,岩石嶙峋的海岸,景色多么迷人!――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皇宫大饭店的侧翼,收费较低廉,以花园与之相连,因此我们这些住在侧楼的人,与大饭店的客人常来常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发生了桩不折不扣的桃色事件。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乘午间列车到了饭店(我必须确切交代他到达的时间,因为时间对这桩绯闻的重要性,不亚于它对激发我们热烈讨论的主题)。他要了间面朝大海的房间:这本身即可说明,此人景况颇为优渥。然而,令他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内敛的雅致,更是他非凡的、极具魅力的俊美:少女般的瘦长脸上,金色的短髭丝绸般抚摩着感性温柔的嘴唇,白皙的额上卷着柔软的波浪状棕发,柔情似水的双眸,每一瞥都像在给人爱抚――他气度温和、热切、和蔼可亲,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惺惺作态。如果说从远处看,他让人联想到大型时装店橱窗里代表男性美、手握精美手杖的玫瑰色蜡人,那么仔细一瞧,任何对他先入为主的纨绔印象均会消失,因为在他身上(极为罕见!),亲切动人与生俱来,就像从他皮肤里长出来的一样。他以同样谦逊诚恳的态度,问候每一个他路过的人。而观察他在各种场合无拘无束地时刻准备展示他的优雅,实在令人赏心悦目。例如他会疾步上前,为某位走向衣帽间的女士提前拿取大衣,他会对每个孩子投以友善的目光,并说上几句俏皮话。他证明了自己既擅长交际,又细致入微――简言之,他一看就是个蒙福之人。这类人从久经考验的感觉中生出自信,深信他们能以潇洒的外表和青春魅力让他人感到愉悦,并将这份自信转化为全新的优雅。对于住在大饭店里,占绝大多数的年老多病的客人来说,他的临在,无疑是种祝福――他迈着青春的胜利步伐,裹挟着轻盈清新的生命之风,正如他的优雅像件礼物,奇妙地赠予一些人,他本人也不可抗拒地步入众人的心田,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他来了才不过两小时,就和里昂来的心宽体胖的工厂主的女儿们――十二岁的安妮特和十三岁的布兰奇打起了网球,而她们的母亲,精致细腻、性格内向的亨丽埃特夫人,看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儿不经意间卖弄风情,与年轻的陌生人眉来眼去,脸上不禁露出轻柔的微笑。晚上,他在我们的棋桌旁观局一小时,期间还悠闲地讲了些精彩的逸闻趣事,随后又陪亨丽埃特夫人,在她的丈夫像往常一样,和一位生意上的熟人玩多米诺骨牌时,去露台上长时间散步。深夜,我注意到他在办公室的暗影里,与大饭店的女秘书交谈,其态度之亲密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的丹麦同伴去钓鱼,同样显露出他在钓鱼方面的绝学,之后和里昂来的工厂主长谈了番政治,又证明了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至少,人们听见这位胖先生爽朗的笑声盖过了阵阵海浪的轰鸣。午饭后――我有必要为了说明情况,准确地交代他在各个阶段的时间分配――我又看见他和亨丽埃特夫人在花园里喝了一小时黑咖啡,和她的女儿们打了一次网球,还在大厅里和那对德国夫妇攀谈。下午六点钟,我去寄信,在火车站遇见他。他急匆匆朝我走来,像是非道歉不可似的跟我说,有人突然叫他回去,但两天后他会再回来。晚饭时,他确实没有出现在餐厅,但这不过是见不着他的身影而已,因为各个餐桌上的人们都在议论他,大伙儿都在纷纷夸赞他轻松乐观的生活态度。
夜里,大概将近十一点,我正坐在房里,想把一本书看完。突然,透过敞开的窗户,我听见花园里不安的叫喊声,大饭店那边显然嘈杂一片。与其说好奇,不如说惊慌,我立即奔到了距离侧楼五十步路的大饭店,发现客人和职工惊慌失措,已然乱作一团。原来亨丽埃特夫人,在她丈夫通常与他来自慕尔的朋友们玩多米诺骨牌的时间去海滨露台散步,此刻却一直未归,于是大家担心她遭遇不测。她那平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