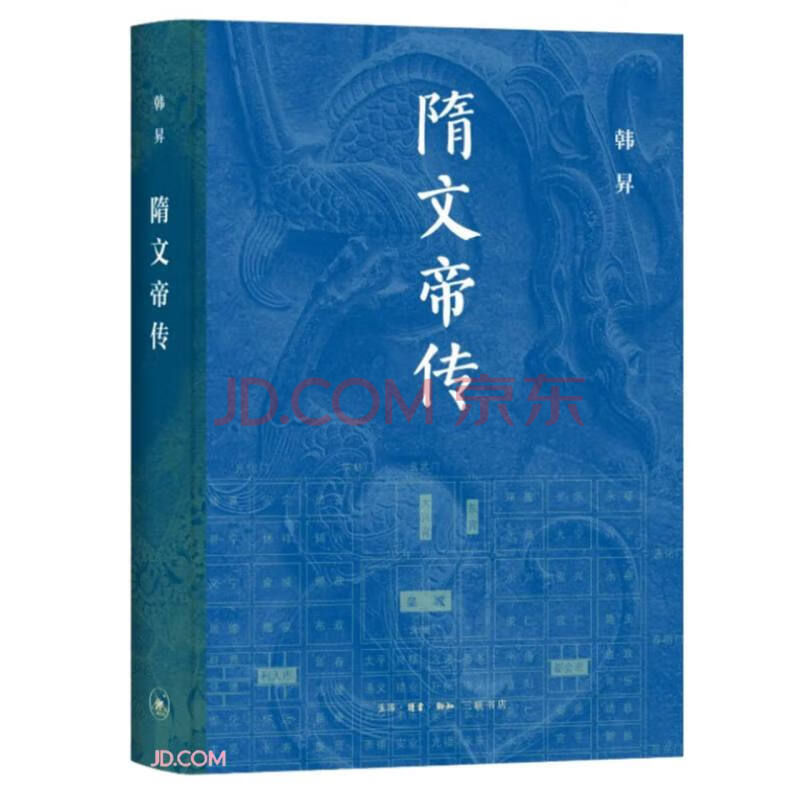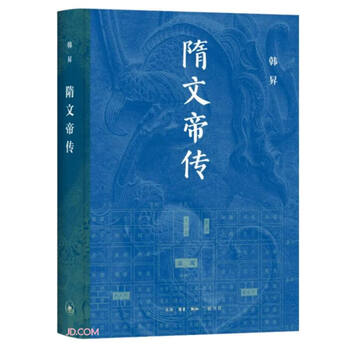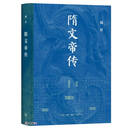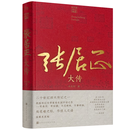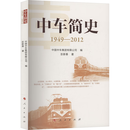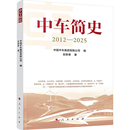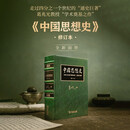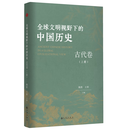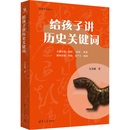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为一代强盛王朝的奠基者,隋文帝以其积极有为与开拓进取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却鲜有人为他单独著书立传。
本书展现了隋文帝杨坚跌宕起伏的一生。作者在考辨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了隋文帝从心怀壮志的贵族少年成长为刚毅果决的政治领袖的完整人生轨迹。隋文帝在人生的前后阶段作风截然不同,光辉和黯淡都十分鲜明。壮年的他开设科举、创立三省六部制、开凿大运河、御侮安邦,让强大的隋王朝立于东亚之巅;而晚年的他迷信佛教、猜忌凶狠、淡漠亲情、滥杀无辜,将专制统治推向顶峰,最终凄楚病逝。
作者并没有苛责隋文帝,而是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审视。隋文帝的一生可以看作隋王朝的缩影,隋朝以及隋文帝的两重性体现了中国从长期分裂迈向统一的复杂性。这一论断引导读者理解门阀政治兴衰、民族融合的深层逻辑,更为解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精彩书摘
第一节 五胡入华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临汾)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唏嘘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参与者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的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存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借此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二百九十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在这场祸乱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借“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少数民族原本文化水平不高,军事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掠夺来激励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在进入中原之后,还必须极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力,把国家政权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后赵末年,石虎(字季龙)的残暴统治天怒人怨,为了转嫁政治危机,他再次祭起民族仇恨的幽灵。
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自西晋主力被击溃之后,中原地区已无法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抵抗,以农耕为业的汉人挡不住少数民族骑兵的暴风骤雨。永嘉之乱后,汉人受尽欺凌虐待,而“汉”字也多为骂语,如汉狗、痴汉、恶汉、汉子、一钱汉、卑劣汉、无赖汉等等,流毒甚远,乃至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亦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其证也。”贱视汉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著的特点。
目录
第一章 艰难时世
第一节 五胡入华
第二节 断裂的社会
第三节 道德沦丧与离心意识
第二章 家世疑云
第一节 “那罗延”的诞生
第二节 弘农杨氏
第三节 武川英豪
第三章 多事之秋
第一节 初入仕途
第二节 “两姑之间难为妇”
第三节 崭露头角
第四节 危险的国丈
第四章 政变建隋
第一节 变起萧墙
第二节 控制京师
第三节 平定三方
第四节 禅让
第五章 除旧布新
第一节 启运开皇
第二节 确立三省六部制
第三节 制定律令礼制
第四节 构建大兴新都
第五节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
第六章 御侮安邦
第一节 塞上风云
第二节 冲破包围
第三节 战略转折
第四节 构建中的世界性帝国
第七章 开皇之治
第一节 勤劳思政
第二节 孝治天下
第三节 继续均田
第四节 整治乡村
第五节 强化财经制度
第六节 增进国力
第八章 君臣之间
第一节 用人政策
第二节 组建新的领导核心
第三节 穿越潜流暗礁
第四节 扬清激浊
第五节 监察防范
第九章 统一大业
第一节 平陈谋略
第二节 直下金陵
第三节 再平江南
第四节 迈向世界
第十章 偃武修文
第一节 寓兵于民
第二节 崇文兴教
第三节 铨选改制
第四节 功成修乐
第十一章 太平志逸
第一节 修仁寿宫
第二节 醉心宗教
第三节 文化统治
第四节 政情异动
第十二章 家族纷争
第一节 独孤皇后
第二节 废黜二王
第三节 改立太子
第十三章 苍凉晚景
第一节 企盼“仁寿”
第二节 大鹏折翼
第三节 凄楚病逝
隋文帝年表
主要引用论著目录
余言
新版后记
试读
第一节 五胡入华
西晋永嘉五年(311),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铁蹄滚滚南下,踏破万里河山。四月,石勒的骑兵在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宁平城追及送西晋太傅司马越之丧的晋军主力,纵兵合击,在撕裂人心的喊杀声中,西晋主力溃于一旦,十余万将士,无一幸免。六月,刘曜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杀戮公卿,挖掘陵墓,尽掠府库,焚烧宫庙,熊熊大火吞没洛阳,吞没几百年的中原文明积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之乱”。经此一役,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
五年之后,也就是西晋建兴四年(316),遭受匈奴刘曜长期围困的长安城,孤立无援,粮尽食绝,城内户不满百,太仓仅剩面饼数十枚,愍帝走投无路,只好乘着羊车,抬着棺材,肉袒衔璧,出城投降,西晋王朝灭亡。
翌年十一月,匈奴皇帝刘聪出城打猎,让愍帝全副武装,持戟前导。平阳(今山西临汾)百姓沿途围观,指指点点;中原父老,唏嘘流涕。十二月,刘聪大宴群臣,令愍帝青衣行酒,执盏洗爵;连刘聪上厕所时,也让愍帝拎着马桶盖,随侍左右。西晋降臣见此光景,不禁悲从中来,尚书郎辛宾抱着愍帝失声痛哭,当场就被拉出去斩首。凌辱折腾够了,年仅十八岁的愍帝还是被打发上黄泉之路,演出了西晋王朝最凄惨、最耻辱的一幕。
招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腐朽无耻的西晋统治者。他们为了争权夺利,满足私欲,不惜发动内战,把锦绣山河沦为一片血海,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更可耻的,是他们竟然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公然勾引胡族为羽党,为其冲锋陷阵,残杀同胞。
首先勾结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是“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参与者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颖以匈奴左贤王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其将兵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结为羽翼;而司马越则招引鲜卑和乌桓入讨司马颖,蹂躏中原。至于边疆大员更是积极勾结胡族,例如都督幽州诸军事的王浚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鲜卑段务勿尘和宇文部的素怒延,以胡族作为其进退割据的军事资本。就这样,毫无道义可言的“八王之乱”演变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统治阶级的内讧发展成为民族对抗。
西晋社会内部本来就潜存着深刻的民族问题。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在农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内徙。西晋王朝既无力阻挡这一趋势,也不能妥善抚绥。官僚豪族甚至趁机掠卖人口,借此大发横财。例如,后赵创建者石勒就曾被东瀛公司马腾所掠卖。因此,在社会的底层,阶级压迫又表现为原始的、自发的民族矛盾。然而,这种低层次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宰全局的政治斗争,却是西晋统治者挑动起来的。
当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斗争之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无不以民族斗争为旗号,劳动者平时受压迫的苦难和胸中的积愤也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最典型的事例如后赵冉闵于都城驱杀胡人。
[冉闵]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这种失去理性、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当时屡见不鲜。真正受尽苦难的是被挑动起来相互仇杀的各族人民。短短的一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从二千二百九十万锐减至一千余万,整个中原沦为废墟。东晋孙绰曾满怀悲凉地控诉道:
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废,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在这场祸乱中真正受益的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借“八王之乱”的机会崛起,将西晋统治者发动的内战转变为推翻西晋王朝的战争。少数民族原本文化水平不高,军事力量也不是那么强大。因此,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掠夺来激励士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在进入中原之后,还必须极力煽动民族仇恨的情绪,以此作为凝聚力,把国家政权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后赵末年,石虎(字季龙)的残暴统治天怒人怨,为了转嫁政治危机,他再次祭起民族仇恨的幽灵。
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自西晋主力被击溃之后,中原地区已无法形成统一的、有组织的军事抵抗,以农耕为业的汉人挡不住少数民族骑兵的暴风骤雨。永嘉之乱后,汉人受尽欺凌虐待,而“汉”字也多为骂语,如汉狗、痴汉、恶汉、汉子、一钱汉、卑劣汉、无赖汉等等,流毒甚远,乃至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3亦言:“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其证也。”贱视汉人,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显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