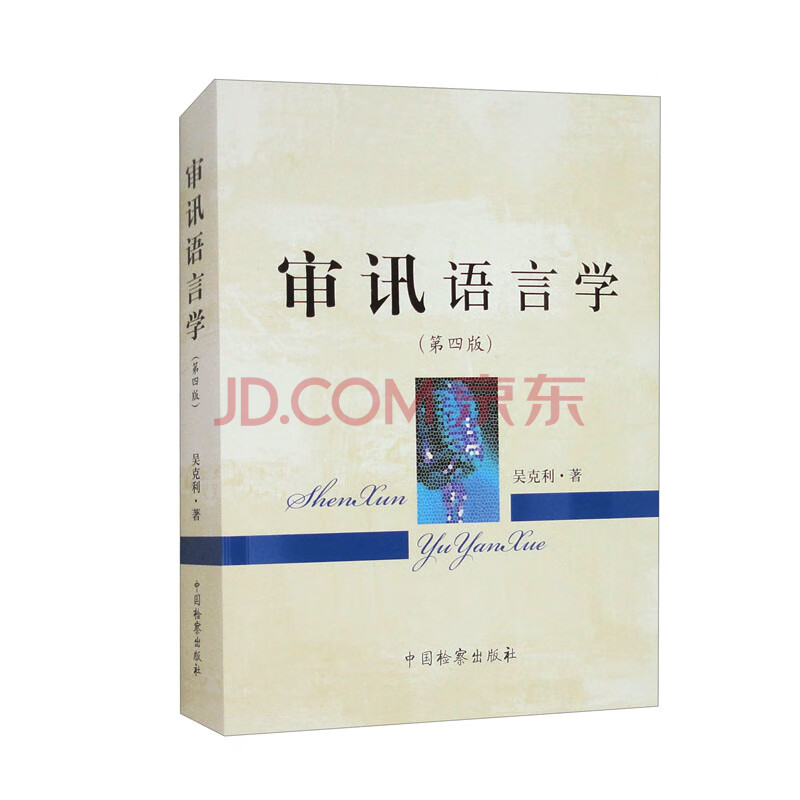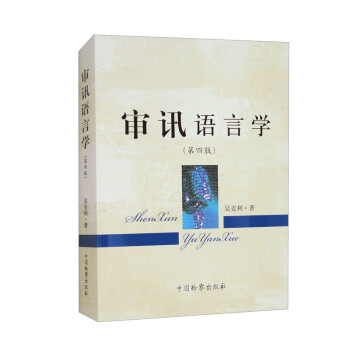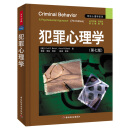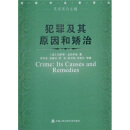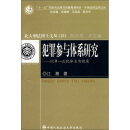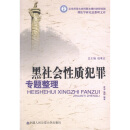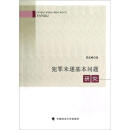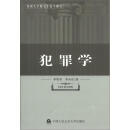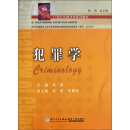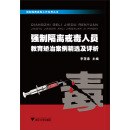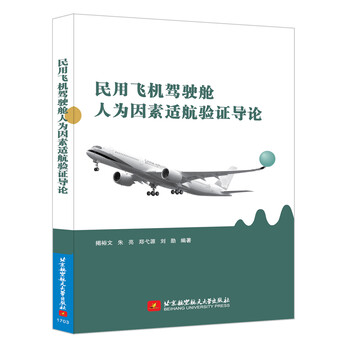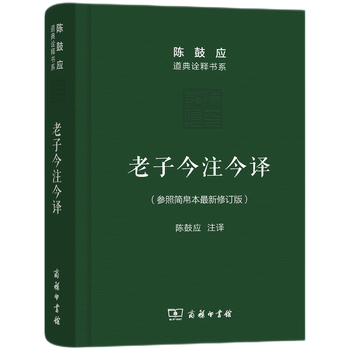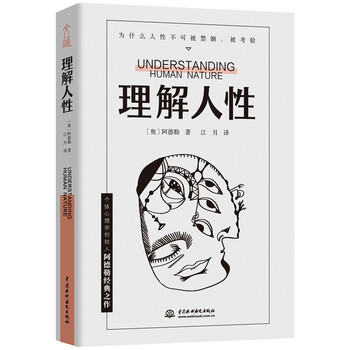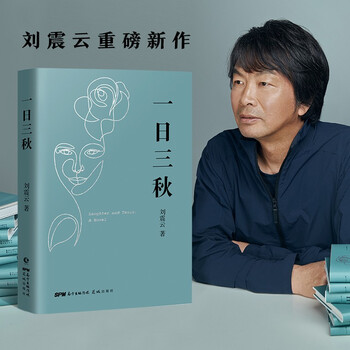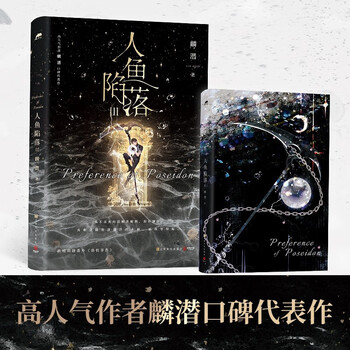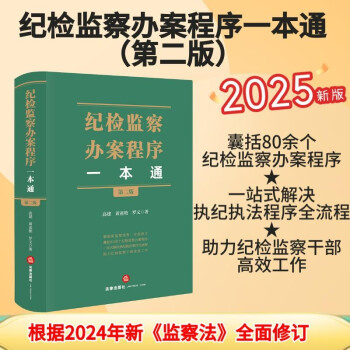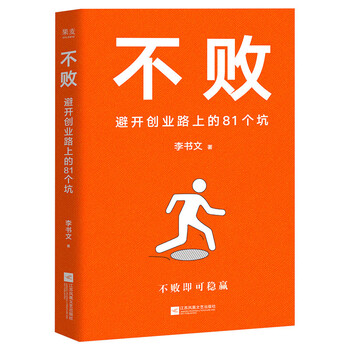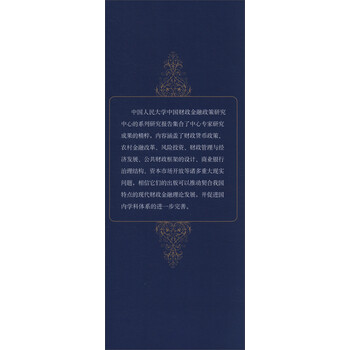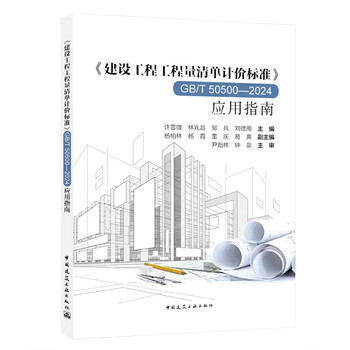内容简介
为规范和科学化做好司法审讯工作,《审讯语言学(第四版)》将法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知识相结合,从司法办案中审讯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聚焦于司法审讯工作中的常见疑难点和工作误区,洞察被审讯人员的心理,系统介绍了审讯语言的运用原理、行为规律和技能技巧;同时辅以鲜活的案例,充分详实地展现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语言对抗技巧与方法,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个成功地审讯现场,将审讯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完美地融合,既填补了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又满足了广大司法实务工作者对审讯教科书的渴求。
目录
第一章 审讯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审讯语言学的概念和性质
第二节 审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第三节 审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形成
第四节 审讯与供述的语用行为冲突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抗审的语用行为路径
第六节 审讯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二章 审讯语言的基本属性
第一节 审讯语言的语音声调
第二节 审讯语言的修辞形式
第三节 审讯语言的表述
第四节 审讯语言的情境
第五节 审讯活动中的无声语言
第三章 审讯语言的语体
第一节 审讯语言的语体特征
第二节 审讯的问答型语言体式
第三节 审讯的劝说型语言体式
第四节 审讯的介入型语言体式
第五节 审讯的定位型语言体式
第六节 审讯的否定型语言体式
第七节 审讯的堵退型语言体式
第四章 审讯的语用行为过程
第一节 审讯的语用行为
第二节 审讯的语言信息
第三节 审讯的语言推理
第四节 审讯语言的原则
第五节 法律阻却事由下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五章 审讯涉案关系的语用行为模式
第一节 审讯涉案关系的语用行为过程
第二节 审讯介入涉案关系的语言模式
第三节 调动审讯空间参与性的语用行为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退路条件选择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退路条件掌控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六章 犯罪嫌疑人抗审心理转换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一节 封控谎言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二节 利用错觉信息确认涉案事实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三节 确认存在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抗审心理支点更换与击破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五节 前提默认涉入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六节 犯罪嫌疑人假想恶性的心理行为属性
第七节 降低恶性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七章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一节 审讯中内部语言的产生
第二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对抗性
第三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心理基础
第四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侦查意识
第五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意志过程
第六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前提条件
第七节 审讯语言信息转移的摄取
第八章 犯罪嫌疑人心理支点更换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一节 犯罪嫌疑人隐瞒对抗的心理支点与退路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前卫心理支点与后卫心理支点更换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三节 犯罪嫌疑人心理需要满足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临界心理状态下的不甘心心理需要的产生与满足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临界心理状态转换供述行为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九章 犯罪嫌疑人谎言抗审的语用行为规律及审讯人员的揭谎与导谎
第一节 犯罪嫌疑人谎言抗审的基本语用行为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谎言的识别方法
第三节 心理测试技术在审讯中的运用
第四节 审讯人员揭谎与导谎的语用行为方法
第十章 审讯活动中肢体语言的语用行为
第一节 犯罪嫌疑人抗审的肢体语言概述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抗审的肢体语言反应
第三节 审讯人员肢体语言的影响
第十一章 犯罪嫌疑人处于不同心理状态下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一节 犯罪嫌疑人抗审行为的心理层面反映定式
第二节 促进犯罪嫌疑人供述动机形成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三节 导入犯罪嫌疑人心理证据的审讯语用行为方法
第四节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限制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六节 审讯人员证据运用的语用行为
第七节 转化犯罪嫌疑人定势心理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八节 犯罪嫌疑人临界心理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九节 犯罪嫌疑人供述矛盾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十二章 知己知彼的审讯语用行为方略
第一节 审讯失败的原因
第二节 审讯语用行为的切入点
第三节 犯罪嫌疑人退路选择的自我评估
第四节 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障碍的支点转移
第五节 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的需要条件
第六节 犯罪嫌疑人隐瞒条件构筑的心理支点的更换
第七节 犯罪嫌疑人涉案原因的心理支点更换方法
第八节 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原因认可的审讯语用行为
第十三章 认知条件下的审讯语用行为技巧
第一节 供述的认知条件
第二节 对抗条件丧失的自我意识的来源
第三节 设置自我意识的认识差异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四节 直达犯罪目标的语用行为
第五节 直达犯罪动机的语用行为
第六节 满足意识存在的语用行为
第七节 剥离犯罪关系的语用行为
第八节 借助关系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九节 再现犯罪心理现场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十节 运用认知概率的语用行为
第十一节 激活间隔心理效应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十二节 审讯的语用行为态势
第十四章 心理置换的审讯语用行为技巧
第一节 趋利避害的供述行为
第二节 心理置换的认知条件
第三节 心理置换的客观条件
第四节 心理置换的支点选择
第五节 亲情置换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六节 求生置换的语用行为技巧
第七
试读
《审讯语言学(第四版)》:
三、犯罪嫌疑人对对抗条件的认知
在通常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轻易供述出自己的犯罪事实,这是由抗审的对抗条件所决定的。侦查审讯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很少主动地向侦查机关供述其犯罪事实。美国刑事司法学界和警察科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弗雷德·英博说,“人类一般不会主动、自发地供认自己的罪行……期望作案人未经审讯的触动便因良心的折磨而供认罪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侦查学鼻祖汉斯·格罗斯也说,“希望每个人都能坦白自己的罪行,是残忍的至少是不人道的”。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具备自我保护的条件下,是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对利益的要求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经过与审讯人员的接触,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自我保护的条件,趋利避害的行为本能告诉他: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为,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都要进行对抗,这是犯罪嫌疑人很少主动地向侦查机关供述其犯罪事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抗条件是决定犯罪嫌疑人对抗行为存在、发展的内部原因,同时,对抗条件也是制约和影响对抗行为存在、发展的外部因素。有条件对抗,犯罪嫌疑人才会选择对抗,如果没有了对抗条件,犯罪嫌疑人就会放弃对抗。由此,犯罪嫌疑人选择的抗审,是在有条件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条件,是建立在犯罪事实没有暴露的基础上的。如果犯罪事实已被侦查机关查清,自己即使不如实供述也不影响司法机关对自己的处罚,在无法逃避损失后果的情况下,就失去了对抗条件,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就失去了意义,自然放弃对抗。“条件”认知的程度决定了犯罪嫌疑人抗审的行为方向。在很多时候侦查审讯人员手里并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犯罪嫌疑人自己交出犯罪证据,犯罪嫌疑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知侦查审讯人员没有掌握自己的犯罪证据,证明自己犯罪还要依赖自己的供述,自己还有条件对抗,那么犯罪嫌疑人能够选择放弃对抗吗?显然不会的。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犯罪嫌疑人在有条件对抗的情况下放弃对抗呢?这是由犯罪嫌疑人对“条件”认知的程度决定的,在审讯活动中,审讯人员的一举一动以及所提供的信息,足以使犯罪嫌疑人感觉到审讯人员已经掌握了犯罪证据,或者是犯罪信息,认知的结果是对抗条件的丧失,这实际上是对“条件”认知的错觉造成的,是误以为“条件”的丧失。这正是审讯人员在没有掌握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的情况下,能够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事实的重要基础。
“对抗条件”的把握程度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对抗程度。对犯罪事实暴露程度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抗条件的认知。全部犯罪事实的暴露与局部犯罪事实的暴露,多个犯罪事实的暴露与部分犯罪事实的暴露,是犯罪嫌疑人选择全部供述还是部分供述的重要基础。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认知是全部的犯罪事实的暴露,那么就有可能选择全部的供述,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认知是部分的犯罪事实的暴露,那么他就不可能选择供述全部的犯罪事实,而会选择暴露多少就供述多少,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审讯活动中审讯人员如何组织犯罪嫌疑人“对抗条件”的认知?是全部的“对抗条件”的丧失,还是部分的“对抗条件”的丧失,是由审讯的目的所决定的。侦查犯罪是全部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局部的犯罪行为,所以审讯人员在组织对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影响时,是让犯罪嫌疑人对全部的犯罪事实的认知,避免犯罪嫌疑人对局部的犯罪事实的认知,如果让犯罪嫌疑人产生的是局部的犯罪事实的认知,那么犯罪嫌疑人只能供述局部的犯罪事实,从而掩盖了其他的犯罪事实。所以“对抗条件”的丧失,是整体的还是个体的,对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犯罪行为的记忆是犯罪嫌疑人“对抗条件”产生的基础。首先侦查审讯是在审讯者预先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而这个前提的产生则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记忆,没有犯罪记忆就不存在对抗,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社会的否定行为,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行为,由此才会引起对抗。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条件”依赖于犯罪的行为记忆,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活动的过程中,那些能够证明犯罪行为的因素和犯罪事实暴露的可能性,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对抗条件”产生了重要影响。犯罪行为的记忆是犯罪嫌疑人自我确认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被审讯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犯罪行为的记忆是犯罪嫌疑人对抗的前提,没有犯罪行为的记忆,就不存在对抗的问题了。在审讯的空间里,对犯罪行为的记忆是模拟产生、再现的,在审讯的空间里,审讯人员对犯罪行为的模拟程度,对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条件的认知有着重要影响。审讯人员模拟的犯罪事实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记忆相吻合,犯罪嫌疑人的对抗条件就会自动丧失,反之就会被强化。再有,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反映,犯罪的行为记忆在审讯人员外来的信息刺激下被激活,自然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出来(这是形体语言研究的结果)。例如,犯罪嫌疑人为了掩
前言/序言
2008年岁末,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法律语言的发展与规范研讨会暨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语言研究会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名专家学者就“法律语言之美”“法律语言之乱”和“法律语言之治”三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有序的研讨。与会者中既有法律语言学的专家,也有法学界的学者,还有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学者型专家。这些具有不同学养和专业经验的人在一起交流,思想的碰撞确实产生了许多精彩的“火花”,令我受益匪浅。我虽然被推选为法律语言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但其实只是法律语言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我认为,法律语言研究特别需要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结合。本书作者吴克利先生大概也属于研究法律语言的业余爱好者。他在检察机关从事反贪侦查工作的二十年中,对审讯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认真总结自己的审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审讯语言的原理、规律和技巧,并且最终写成了这部《审讯语言学》,填补了我国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确实难能可贵。
法律是以语言为生命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法律存在的形式,而且因为语言是法律精神的体现。法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来维持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和稳定性,而这种功能只有借助语言才能实现。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虽然这种精神是不依赖于语言而存在的,但是只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实际上,正是在法律规定的字里行间,人们才可以领悟到法律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没有人类的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法律的人都应该研究法律语言。
在法学领域中,法律语言学与证据学之间又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首先,语言和证据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就事物的属性而言,语言天然就是一种证据。或者说,语言是证据的自然表现形式之一。在司法证明中使用的证据一般都离不开语言。且不说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证据的基本内涵就是语言,即使是各种各样的物证,其证明功能的实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例如,物证提取人员的证言或笔录,物证鉴定人员的鉴定结论或意见等。其次,语言学和证据学在研究对象和目标上存在相似性。顾名思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证据学的研究对象是证据,二者似乎并不相同。但是,这种差异具有表象的性质。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具有相似性。例如,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七何”,即何人(什么人说的)、为何(为什么说的)、何时(在什么时间说的)、何地(在什么地点说的)、对何(对什么人说的)、如何(怎么说的)、何语(说的什么)。因此,语言学的研究目标可以概括为:何人为何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如何说了何语。在证据学研究中,司法证明的对象也可以概括为“七何”,即何人、为何、何时、何地、何物、如何、何事。因此,证据学的研究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何人为何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物如何干了何事。最后,法律语言学的产生也与证据学存在密切联系。所谓“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大概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而且其最初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庭审判中面临的语言识别问题,例如,根据语言特征判断使用者的身份和分析证人证言的准确含义等。当法官在审判中面临这类难题时,语言学家就会出庭作证,提供关于语言识别和语言分析的专家证言。其实,英文中的“法律语言学”是Forensic Linguistics,直译应为“司法语言学”或“法庭语言学”,属于司法证明领域内语言识别的范畴,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特征对使用者进行人身同一认定。这是法律语言学和证据学之联系的历史渊源。现在,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法律语言学”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司法证明活动中的语言识别,而是发展到对法律语言的全面研究,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侦查人员在职业活动中使用的语言。
对于上述人员来说,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职业行为技能,而这在审讯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讲,审讯就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语言对抗。审讯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讯人员使用语言的能力和技巧。优秀的审讯人员在审讯中可以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通过语言来完成审讯任务。而那些使用刑讯逼供的审讯人员往往也是因为自身的语言能力不强,只好借助暴力行为来获取口供。由此可见,研究审讯语言不仅可以提高审讯的效率,而且可以降低审讯人员对刑讯行为的依赖。在中国的犯罪侦查活动正在走向文明与法治的今天,审讯语言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吴克利先生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亲身参加过许多重大疑难案件的审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审讯经验。而且他认真学习,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在最近几年中连续写出了多部关于审讯的专著,包括《贪污、贿赂案件的审讯技巧》《审讯心理攻略》《审讯心理学》等。在这部《审讯语言学》中,他从审讯工作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系统介绍了审讯语言的运用原理、行为规律和技能技巧,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用价值。因此,我诚挚地向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