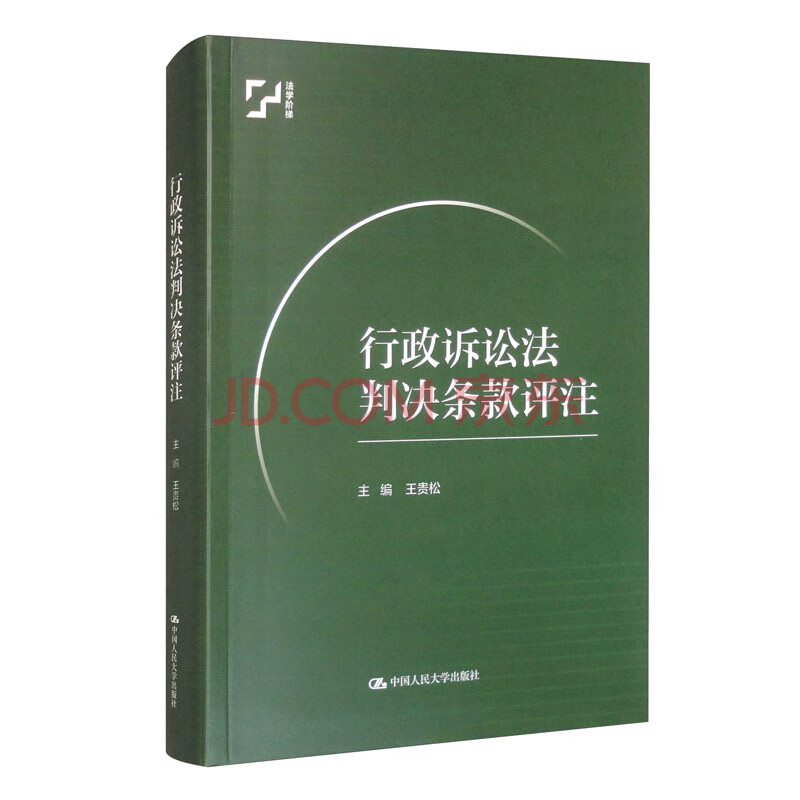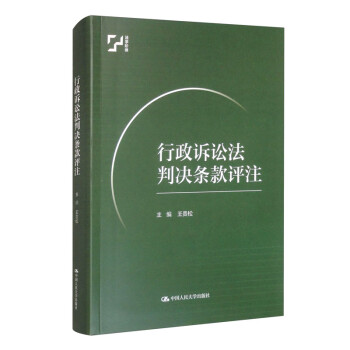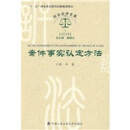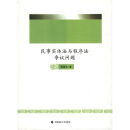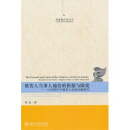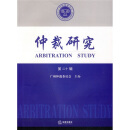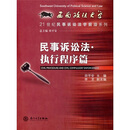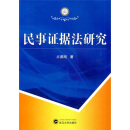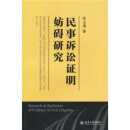内容简介
《行政诉讼法判决条款评注》是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关于判决类型的条款的评注,遵照严格的法律解释方法,对《行政诉讼法》中的判决类型条款作出以适用为导向的解释,力图通过融合立法、司法与理论,回答特定法条在法律适用中的一切问题。
考虑到《行政诉讼法》不同条文在整部法律中的重要性、适用性的不同,作者特选择了该法中既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又与实践密切关涉的条文进行集中评注,分别是驳回判决、撤销判决、禁止反复效力、履行判决、给付判决、确认违法判决、确认无效判决、确认判决的责令补救和赔偿、变更判决、行政协议宿舍判决、复议决定的一并裁判、二审裁判、当事人的履行义务、对私人的执行、对行政机关的执行,涵括了行政诉讼法中所有的判决种类。
精彩书摘
《行政诉讼法判决条款评注》:
二、驳回判决的适用情形
与2000年《行诉法解释》规定的驳回判决适用情形不同,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9条只规定了两种适用情形:其一是行政行为合法,其二是原告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这一规定实际上也将行政诉讼判决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关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决,另一类是关于原告请求的理由能否成立的判决。
(一)行政行为合法
《行政诉讼法》第69条前半句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适用驳回判决。这些要件是与撤销判决、确认违法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和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相对应的。这里姑且将这种判决称作行政行为合法型驳回判决。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中的维持判决适用情形的规定是相同的。这一句的适用是以存在行政行为为前提的。不过,这里的行政行为并没有被区分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如果是羁束行政行为,仅此三个要件,判断其为合法,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裁量行政行为,则显然不足。既然未作区分,那么,在三个要件的理解上可能产生问题:是满足这三个要件就适用驳回判决,还是还需要满足更多的要件才能适用驳回判决?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均属于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与撤销判决等适用的行政行为情形相比,驳回判决适用的行政行为合法除了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还不能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情形,否则就需要适用撤销判决等肯定性判决。有法官认为,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可能并不止该三种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只有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情况下,才满足行政行为合法的所有条件。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都是相对确定的概念,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法官认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需广义理解,而不能与第70条第2项中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量齐观。其原因在于,第70条对行政行为不合法与第69条对行政行为合法所采用的标准并不完全吻合。这里的“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少应包括:第一,行政行为的内容必须在法律、法规赋予该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第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必须是与本案法律关系相适应的法律规范,行政行为在法律适用方面不存在表达上和文字上的技术性错误。①这种观点其实是想将证据和程序之外的所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都归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问题。当然,证据、程序问题也都会反映为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性问题,只是突出强调而已。所有问题终归为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性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作广义解释,将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理解为行政行为完全合法的要求,更为妥当,而不宜将三项要求理解为只是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不完全列举。只有完全符合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才能确认行政行为合法,进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从判断方法上,这可被称作综合判断型驳回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合法要件负有举证责任。
与《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1项规定“主要证据不足”不同,第69条前半句规定的是“证据确凿”,这也意味着在证据方面,不仅要具备证明要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还要具备确定效果所需的次要证据,而且还要达到确凿的程度。在上诉审驳回判决的适用条件方面,《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与“事实清楚”的内涵是一致的。在实务中,有时会因行政行为多种多样,在证明上是否达到“证据确凿”的要求而发生分歧。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少主张,应当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来判断构成确凿的证据。不过,这更多地属于证据法上的证明标准问题,“证据确凿”的要求可以涵盖多种可能性。
当然,《行政诉讼法》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还可以有一种解释的可能,它不是对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规定,而是对原告可能攻击的情形的规定。也就是说,原告提出某诉讼请求,理由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法院对此展开审查,在原告声称的理由不成立时,法院即作出驳回判决。这时,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只是行政行为合法理由的列举而已。不过,理论和实务界一般不作这种理解,而且,《行政诉讼法》第49条只是要求原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并未就诉讼请求成立的理由进一步提出要求。实务中,即便原告没有提出被告的权限问题,法院通常从被告的主体权限开始审查,但这种审查基本上是在没有合法性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在没有合法性问题或者当事人无争议的情况下,法院的审查是没有意义的。在原告缺乏相应认识时,法院在释明指出之后再予审查,既合乎不告不理的原则,也有助于纷争的一次性解决。
……
目录
第69条(驳回判决)
一、规范沿革与规范意旨
(一)驳回判决的确立
(二)驳回判决的定位
二、驳回判决的适用情形
(一)行政行为合法
(二)原告请求的理由不成立
(三)诉讼请求不成立的其他情形
三、驳回判决的效力
(一)驳回判决效力的内容和界限
(二)驳回判决的执行问题
第70条(撤销判决)
一、规范沿革与体系定位
(一)规范生成
(二)规范变迁
(三)体系定位
二、撤销判决的适用对象
(一)改用“行政行为”术语的考量
(二)作为撤销判决适用对象的“行政行为”
三、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
(一)主要证据不足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三)违反法定程序
(四)超越职权
(五)滥用职权
(六)明显不当
四、撤销判决的适用结果
(一)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
(二)责令重作
第71条(禁止反复效力)
一、规范沿革与规范意旨
(一)规范沿革
(二)规范意旨
二、禁止反复效力的基础
(一)撤销判决
(二)其他类型判决
三、禁止反复效力的范围
(一)客观范围
(二)主体范围
(三)时间范围
四、禁止反复效力的实现
(一)两种并行的性质
(二)具体的实现方式
(三)实现的辅助要求
第72条(履行判决)
一、规范演变与核心要义
(一)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判决初创
(二)2000年《行诉法解释》的要件解释
(三)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后的类型分野
(四)2018年《行诉法解释》的构造填充
二、履行判决的体系定位
三、履行判决的前置条件与适用条件
(一)前置条件
(二)客观要件: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
(三)主观要件:原告享有履职请求权
(四)请求权审查模式下主客观要件的统合
四、履行判决的裁判构造与其他问题
……
第73条(给付判决)
第74条(确认违法判决)
第75条(确认无效判决)
第76条(确认判决的责令补救和赔偿)
第77条(变更判决)
第78条(行政协议诉讼判决)
第79条(复议决定的一并裁判)
第89条(二审裁判)
第94条(当事人的履行义务)
第95条(对私人的执行)
第96条(对行政机关的执行)
事项索引
试读
《行政诉讼法判决条款评注》:
二、驳回判决的适用情形
与2000年《行诉法解释》规定的驳回判决适用情形不同,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9条只规定了两种适用情形:其一是行政行为合法,其二是原告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这一规定实际上也将行政诉讼判决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关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决,另一类是关于原告请求的理由能否成立的判决。
(一)行政行为合法
《行政诉讼法》第69条前半句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适用驳回判决。这些要件是与撤销判决、确认违法判决、确认无效判决和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相对应的。这里姑且将这种判决称作行政行为合法型驳回判决。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与1989年《行政诉讼法》中的维持判决适用情形的规定是相同的。这一句的适用是以存在行政行为为前提的。不过,这里的行政行为并没有被区分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如果是羁束行政行为,仅此三个要件,判断其为合法,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裁量行政行为,则显然不足。既然未作区分,那么,在三个要件的理解上可能产生问题:是满足这三个要件就适用驳回判决,还是还需要满足更多的要件才能适用驳回判决?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均属于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与撤销判决等适用的行政行为情形相比,驳回判决适用的行政行为合法除了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还不能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等情形,否则就需要适用撤销判决等肯定性判决。有法官认为,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可能并不止该三种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只有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无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明显不当的情况下,才满足行政行为合法的所有条件。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都是相对确定的概念,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法官认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需广义理解,而不能与第70条第2项中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等量齐观。其原因在于,第70条对行政行为不合法与第69条对行政行为合法所采用的标准并不完全吻合。这里的“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少应包括:第一,行政行为的内容必须在法律、法规赋予该机关的权限范围之内;第二,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原则和精神;第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必须是与本案法律关系相适应的法律规范,行政行为在法律适用方面不存在表达上和文字上的技术性错误。①这种观点其实是想将证据和程序之外的所有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都归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问题。当然,证据、程序问题也都会反映为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性问题,只是突出强调而已。所有问题终归为适用法律、法规的正确性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作广义解释,将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理解为行政行为完全合法的要求,更为妥当,而不宜将三项要求理解为只是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不完全列举。只有完全符合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才能确认行政行为合法,进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从判断方法上,这可被称作综合判断型驳回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符合合法要件负有举证责任。
与《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1项规定“主要证据不足”不同,第69条前半句规定的是“证据确凿”,这也意味着在证据方面,不仅要具备证明要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还要具备确定效果所需的次要证据,而且还要达到确凿的程度。在上诉审驳回判决的适用条件方面,《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是“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与“事实清楚”的内涵是一致的。在实务中,有时会因行政行为多种多样,在证明上是否达到“证据确凿”的要求而发生分歧。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少主张,应当确立不同的证明标准,来判断构成确凿的证据。不过,这更多地属于证据法上的证明标准问题,“证据确凿”的要求可以涵盖多种可能性。
当然,《行政诉讼法》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还可以有一种解释的可能,它不是对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规定,而是对原告可能攻击的情形的规定。也就是说,原告提出某诉讼请求,理由是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法院对此展开审查,在原告声称的理由不成立时,法院即作出驳回判决。这时,第69条前半句的规定只是行政行为合法理由的列举而已。不过,理论和实务界一般不作这种理解,而且,《行政诉讼法》第49条只是要求原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并未就诉讼请求成立的理由进一步提出要求。实务中,即便原告没有提出被告的权限问题,法院通常从被告的主体权限开始审查,但这种审查基本上是在没有合法性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在没有合法性问题或者当事人无争议的情况下,法院的审查是没有意义的。在原告缺乏相应认识时,法院在释明指出之后再予审查,既合乎不告不理的原则,也有助于纷争的一次性解决。
……
前言/序言
《行政诉讼法》自1990年实施至今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于2014年修正后实施也有了十年的光景。
《行政诉讼法》的每一个条文都得到过实践,大多数条文都得到过讨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产生了林林总总的问题。如何给法律实践提供适当指引?如何凝聚共识、减少适用歧义?撰写法律评注无疑是可行的路径之一。
近年来民法学者和刑法学者的示范为行政诉讼法评注的撰写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行政诉讼法的深入实施也为行政诉讼法评注的撰写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行政诉讼法判决条款评注》关于行政诉讼法判决条款的评注,可谓是行政法学界的首次尝试,因为经验有限,写法与成熟的评注体裁或许尚有距离,但必定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也会有助于凝聚并拓展有关行政诉讼法的共识,稳步推动行政诉讼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