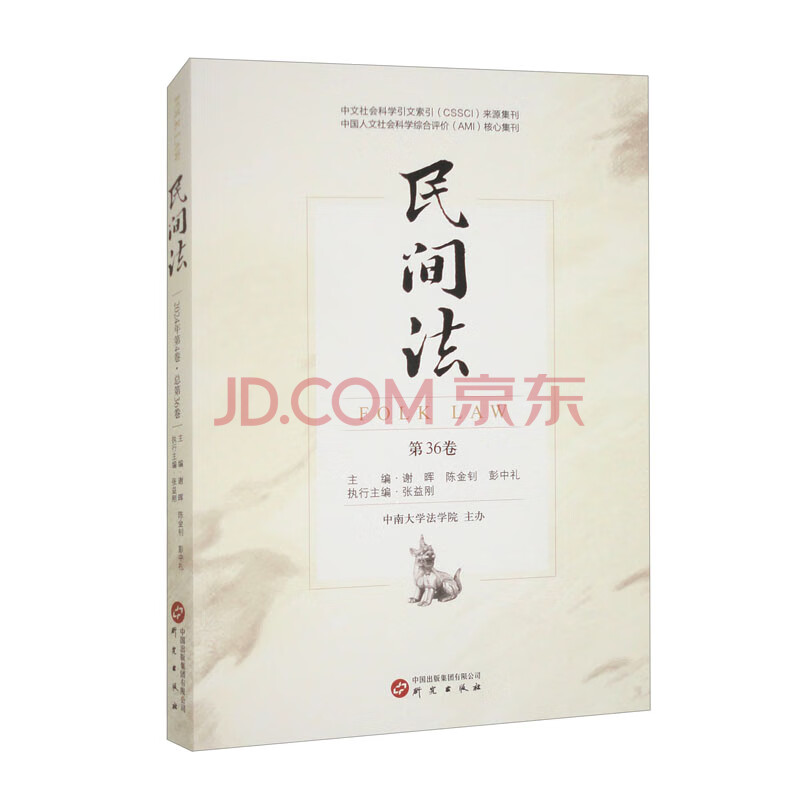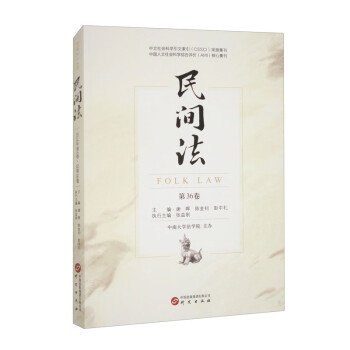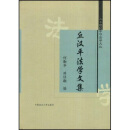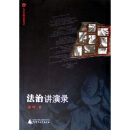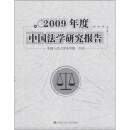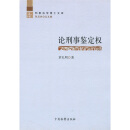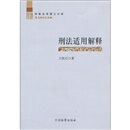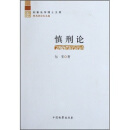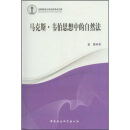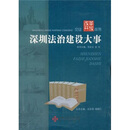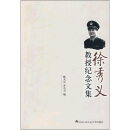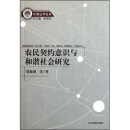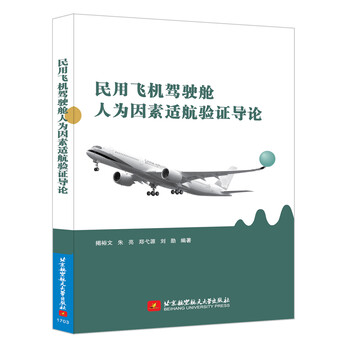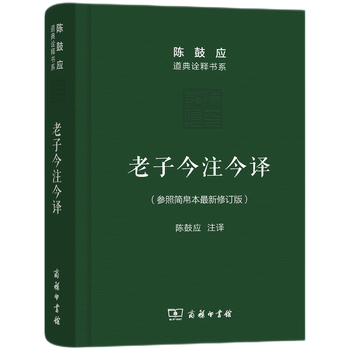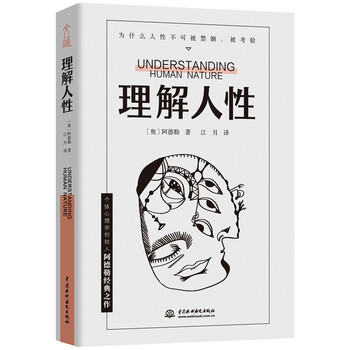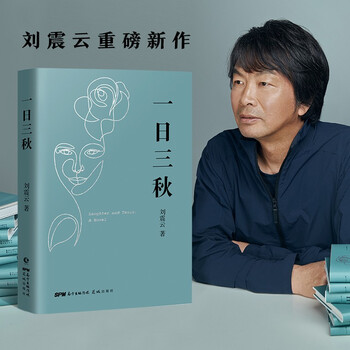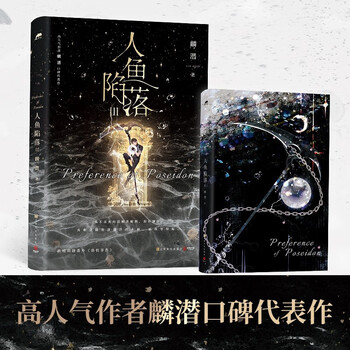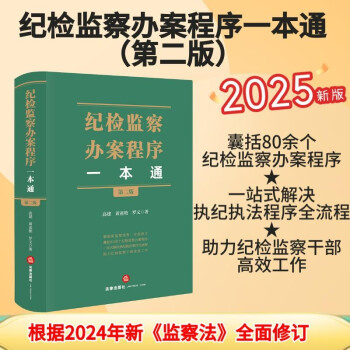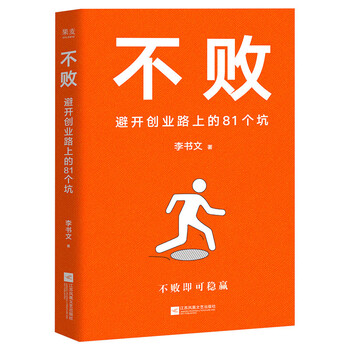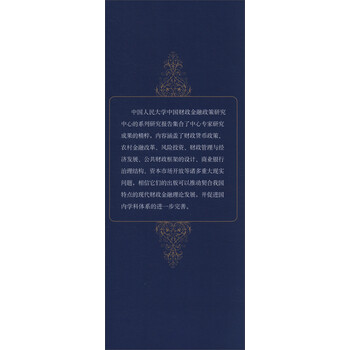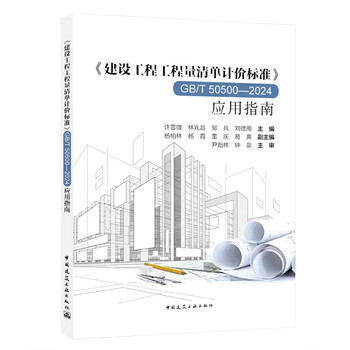内容简介
自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秩序,既因国家正式法而成,亦藉民间非正式法而就。然法律学术所关注者每每为国家正式法。此种传统,在近代大学法学教育产生以还即为定制。被谓之人类近代高等教育始创专业之法律学,实乃国家法的法理。究其因,盖在该专业训练之宗旨,在培养所谓贯彻国家法意之工匠——法律家。
目录
总序/原序
村规民约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困境与提升
民间规范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适用场域与法治化路径
生态法治中的传统秩序:裕固族环境习惯法的内涵、类型及当代启示
新时代村规民约的环境法治功能定位及机制构造
法理讨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的遵守机制探析
区块链:代码自治的法律幻象
法律人类学在荷兰——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论国家政策概念的功能主义阐释——兼与彭中礼教授商榷
制度分析
警察执法的多重角色与行动逻辑——以110接处警为素材
“和合文化”视野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以双向保护为基本价值
在线纠纷解决的法律规制研究
村民将习惯灌溉用水权转让给工业用水人之行为效力判定——由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论我国继承协议的制度形塑
公证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和路径探索——以公证提存为视角
经验解释
著作权司法裁判中的政策考量——以翻译合理使用为研究视角
清代长随文献的版本及其史料价值
民事裁判中村规民约适用问题研究——基于31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国家在场”视角下曲艺普法的行动逻辑与完善路径——以X县曲艺普法者F某为个案分析
实质性解决争议:行政协议纠纷法院调解的现状及优化路
域外经验
被遮蔽的“正当性”——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回顾与展望:对中国留日法学“课程博士”学位论文的考察(1978-2023)
论法与道德的问题
前言/序言
在我国,从梁治平较早提出“民间法”这一概念起算,相关研究已有25年左右的历程了。这一概念甫一提出,迅即开启了我国民间法研究之序幕,并在其后日渐扎实地推开了相关研究。其中《民间法》《法人类学研究》等集刊的创办,一些刊物上“民间法栏目”的开办,“民间法文丛”及其他相关论著的出版,一年一度的“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类学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年会、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专业委员会年会等的定期召开,以及国内不少省份民族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年会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可谓是相关研究蓬勃繁荣的明显标志和集中展示。毫无疑问,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学术成果,已经有了可观的量的积累。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出现学术研究“卡脖子”的现象。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民间法”研究在量的积累上突飞猛进,但另一方面,真正有分量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因此,借起草“《民间法》半年刊总序”之机,我愿意将自己对我国当下和未来民间法研究的几个“看点”(这些思考,我首次通过演讲发表在2020年11月7日于镇江召开的“第16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抛出来,作为引玉之砖,供同仁们参考。
第一,民间法研究的往后看。这是指我国的民间法研究,必须关注其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即关注作为历史文化积淀和传承的民间法。作为文化概念的民间法,其很多分支是人们社会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特别是人们习常调查、研究和论述的习惯法——无论民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宗族习惯法,还是社团习惯法、行业习惯法、宗教习惯法,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一个宗族,或者一个社团、一种行业、一种宗教在其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的结果。凡交往相处,便有规范。即便某人因不堪交往之烦而拒绝与人交往,也需要在规范上一视同仁地规定拒绝交往的权利和保障他人拒绝交往的公共义务。当一种规范能够按照一视同仁的公正或“正义”要求,客观上给人们分配权利和义务,且当这种权利义务遭受侵害时据之予以救济时,便是习惯法。所以,民间法研究者理应有此种历史感、文化感或传统感。应当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和气概,在历史中观察当下,预见未来。把史上积淀的民间法内容及其作用的方式、场域、功能,其对当下安排公共交往、组织公共秩序的意义等予以分门别类,疏证清理,发扬光大,是民间法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在这方面,我国从事民族习惯法,特别是从史学视角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但未尽之业仍任重道远。其他相关习惯法的挖掘整理,虽有零星成果,但系统地整理研究,很不尽人意。因之,往后看的使命绝没有完成,更不是过时,而是必须接续既往、奋力挖掘的民间法学术领域。
第二,民间法研究的往下看。这是指我国的民间法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性,即关注当代社会交往中新出现的民间法。民间法不仅属于传统,除了作为习惯(法)的那部分民间法之外,大多数民间法,是在人们当下的交往生活中产生并运行的。即便是习惯与习惯法的当下传承和运用,也表明这些经由历史积淀所形成的规则具有的当下性或当下意义。至于因为社会的革故鼎新而产生的社区公约、新乡规民约、企业内部规则、网络平台规则等,则无论其社会基础,还是其表现形式和规范内容,都可谓是新生的民间法。它们不但伴随鲜活的新型社会关系而产生,而且不断助力于新社会关系的生成、巩固和发展。在不少时候,这些规范还先于国家法律的存在,在国家法供给不及时,以社会规范的形式安排、规范人们的交往秩序。即便有了相关领域的国家法律,但它也不能包办、从而也无法拒绝相关新型社会规范对人们交往行为的调控。这在各类网络平台体现得分外明显。例如,尽管可以运用国家法对网络营运、交易,论辩中出现的种种纠纷进行处理,但在网络交往的日常纠纷中,人们更愿意诉诸网络平台,运用平台内部的规则予以处理。这表明,民间法这一概念,不是传统规范的代名词,也不是习惯规范的代名词,而是包括了传统规范和习惯规范在内的非正式规范的总称。就其现实作用而言,或许当下性的民间法对于人们交往行为的意义更为重要。因此,在当下性视角中调查、整理、研究新生的民间规范,是民间法研究者们更应努力的学术领域。
第三,民间法研究的往前看。这是指我国的民间法研究,不仅应关注过去、关注当下,而且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及其规范构造要有所预期,发现能引领未来人们交往行为的民间法。作为“在野的”、相对而言自生自发的秩序安排和交往体系,民间法不具有国家法那种强规范的可预期性和集约性,反之,它是一种弱规范,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弥散性。故和国家法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时滞性”相较,民间法更具有对社会关系“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即时性特征。它更易圆融、自然地适应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发展,克服国家法在社会关系调整中过于机械、刚硬甚至阻滞的特点。惟其如此,民间法与国家法相较,也具有明显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