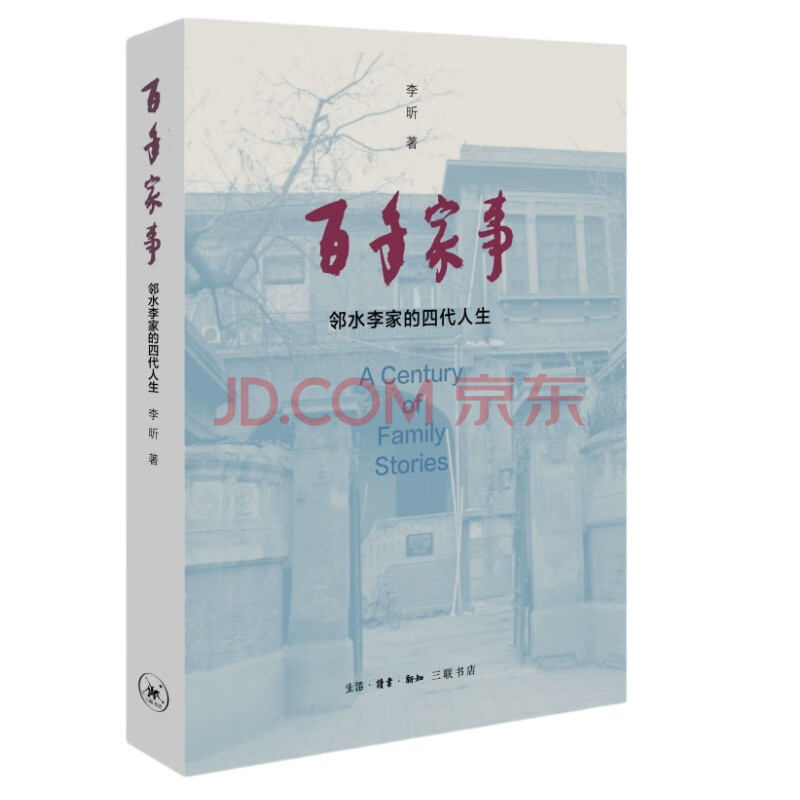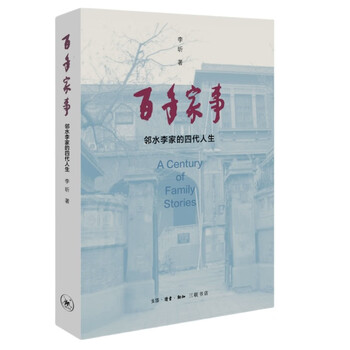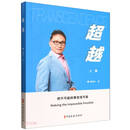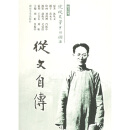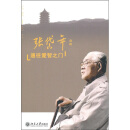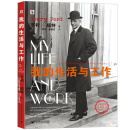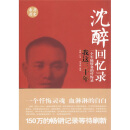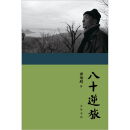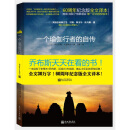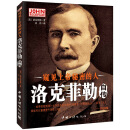内容简介
《百年家事》无意为家族的前辈树碑立传、歌功颂德,而是以人物侧写的方式,把晚清实业家、水师提督、清华教授、共和国出版人的家族故事,串联起来。官场上的宦海沉浮、外交中的刀光剑影、书斋里的理想情怀、激情年代的奇遇人生,都在不虚构、不浮夸、不矫饰、不为尊者讳的前提下,纪实呈现。纵贯四代人的一百年,横跨三世纪的光影线索,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让读者对时代的离合、家庭的悲欢、命运的跌宕,产生近距离的认识。
精彩书摘
作者笔下,朝代更替,最难交代的背景家世写来坦坦荡荡,没有纠结,写老人家独立的人格,文字风格优雅不见溢美,说难言之隐清可见底,不存芥蒂,分析复杂的世局三言两语如庖丁解牛,写父子连心处至情至文感人下泪,写大时代穿插一些小故事活泼生动。——最难写的人物就是父亲,古往今来留下的好文章很少。
——旅美作家 王鼎钧
《百年家事》以四代主要人物的相关事件为中心,清理现象,掀开谜团,甚至直面苦难。若与同类家史与自传性书籍相比,此书在叙述的真实性、资料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四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书中的许多细节既呈现李家人之于真相、真理的追求,又始终不缺人性的温情与爱,这正是不少囿于宏大叙事的史书所欠缺的。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怎能见不到人,感受不到有温度与真善美的文字呢?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郭世佑
《百年家事》是文献研究与亲身经历的回忆、口述结合。作者的文献考证旁征博引,分析细致,逻辑严谨,更难得的是不为尊者亲者隐讳;他的回忆,更多文献所阙如的细节,这种细节不仅更加生动,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变化,弥足珍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院 雷颐
目录
序一:直陈磨难,信史可期 郭世佑
序二:家族史与集体记忆 雷颐
自序
我的曾祖父李征庸
第一次广州起义中的李征庸
李准人生中的两个焦点
附录:有关李准的几个疑问
冤家恩公——李准与岑春煊的恩恩怨怨
李准与汪精卫
我的祖母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吊诡人生——我的癌症故事
我的大学梦
试读
作者笔下,朝代更替,最难交代的背景家世写来坦坦荡荡,没有纠结,写老人家独立的人格,文字风格优雅不见溢美,说难言之隐清可见底,不存芥蒂,分析复杂的世局三言两语如庖丁解牛,写父子连心处至情至文感人下泪,写大时代穿插一些小故事活泼生动。——最难写的人物就是父亲,古往今来留下的好文章很少。
——旅美作家 王鼎钧
《百年家事》以四代主要人物的相关事件为中心,清理现象,掀开谜团,甚至直面苦难。若与同类家史与自传性书籍相比,此书在叙述的真实性、资料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四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书中的许多细节既呈现李家人之于真相、真理的追求,又始终不缺人性的温情与爱,这正是不少囿于宏大叙事的史书所欠缺的。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怎能见不到人,感受不到有温度与真善美的文字呢?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郭世佑
《百年家事》是文献研究与亲身经历的回忆、口述结合。作者的文献考证旁征博引,分析细致,逻辑严谨,更难得的是不为尊者亲者隐讳;他的回忆,更多文献所阙如的细节,这种细节不仅更加生动,而且更能反映时代、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变化,弥足珍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院 雷颐
前言/序言
自序
四川省邻水县这个地名,很长时间以来,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说是熟悉,因为我从小被父亲告知,在各种履历表“籍贯”一栏,要填上它,我甚至在看不懂地图、不知它的方位时就已经熟知这个名称;说是陌生,因为我对它没有一点感性认知,直到2007年55岁时,我得知这个县城距离重庆只有一百多公里,才借着参加重庆书展的机会,找了一辆便车去了一趟。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里作为我的“籍贯”。我问父亲,这是你的出生地吗?父亲说也不是,他出生在他的伯父、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旧宅里,地点在广州的东园。他说邻水是我祖父的出生地,因而就是我的祖籍。但后来我查了李准自编年谱,得知他说的都不对,我父亲李相崇1914年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后李准在香港购置的罗便臣道23号寓所,而我祖父李涛1894年出生在我曾祖父李征庸担任知县的广东揭阳县(今揭阳市)县衙内。说起来,邻水只是我曾祖父李征庸和伯祖父李准的出生地。
我们李家本是江宁府(今南京)上元县李家村人,先祖李诣元在康熙年间朝廷拔贡[1]获选为四川顺庆府邻水县教喻[2],从而落业于邻水龙安镇河堰坝,后迁居邻水柑子镇李家坝,至我曾祖父李征庸是第九世,我伯祖父李准和祖父李涛是第十世。曾祖父有两房夫人,育有两儿两女,年龄相差得十分悬殊。李准1871年出生,比1894年出生的弟弟李涛年长23岁。曾祖父李征庸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钦点刑部贵州司主事,第二年因高祖突然病逝,返乡守孝,本应丁忧三年,但他此间在邻水开矿建厂多家,上了操办实业的瘾,八年乐而忘归。后因遭到乡人嫉妒,才返京候命,1887年获选广东河源县(今河源市)知县。此后他将一家人带出了邻水,本人再也不曾回乡。他在广东各地任职,在河源、香山、揭阳、南海等地当过知县,全家人也跟着他四处迁徙。他去世前两年曾被授三品卿衔,任四川矿物商务大臣,准予专折奏事,但他在此任上也没有到过邻水,甚至是否回过四川,都很难说。他1901年病逝于广州,停灵于广州郊外,灵柩直到1905年才被李准护送归葬故里。至于李准,因为就在这一年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也便带着家人(包括我祖父一家)长居广州,辛亥后虽是挂冠而去,却也是定居香港和天津,再没有机会重回四川的。
所以2007年我回邻水寻根,发现五服内的族人,与我同曾祖的已经没有了,同高祖的都不认识、无联系。这些族人带我祭拜了高祖墓,参观了曾祖父当年开设学堂的破旧砖瓦房。族人们很以我曾祖父、伯祖父为荣,因为这是当地李家走出的两位高官,特别是李准,在保卫南海问题上还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说,当地正在打造李准文化品牌,把他和广安地区(邻水县属于广安地区)的另外两位名人一起宣传,我问另外两位名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邓小平和双枪老太婆。我听了很有一些惊讶。
其实也不能说李征庸在邻水绝对没有后人。1887年,有人在山上竹林中捡到一个弃婴交给李准母亲抚养,取名李澂,人称“竹林君”。此时李征庸在外任职不知此事,孩子是夫人私自收养的。不想这孩子生性顽劣,不成器,李准母亲伤透脑筋,总是担心自己教养失职犯了大错。几年后,在她去世之前,把李准叫到面前,嘱咐李准一定要把他调教成才,方才闭眼。此后这位“竹林君”也长期跟随李准,他比我祖父李涛大七岁,根据李家大排行,李准称他七弟,称我祖父八弟,待他亦如手足。1901—1902年,李准曾请在广州番禺中了案首[3]的汪兆铭[4]来给自家的孩子做家教,学生有多人,包括李准的长子李相枚和八弟李涛,也有李澂。1903年汪兆铭赴日本留学,当时李澂16岁,李准把他托付给汪兆铭带到日本。谁知此人一身恶习不改,到了日本即退学,成了流民,李准千呼百唤而不归。直到两年后派人将其送回国内,关在铁屋中。为“收其野心”,李准为其娶妻,后令其返回邻水定居。
李准对这个收养而来的弟弟没有出息深感自责,他在回忆录中多次感叹:“陷此弟于不肖,我之过也。”当然他也不能信任此人。李澂在邻水,但李准从不提起他。李征庸当年在邻水办实业,是有家族企业的,这些企业由李准继承,但李准宁可托几位侄子管理,也不找李澂。但侄子们也不得力,不过是享受李家企业带来的利益罢了。李准晚年,生活贫困,需要老家经济支持,但这些子侄竟然不肯援手,他在回忆录里多次慨叹:“家中款项亦难接济,屡电催之,亦不应。”“自宅子侄均不可恃。”“川中仍不来一钱,穷困达于极点。”[5]至于李澂,其人回乡后即成为恶霸地主,1951年在土改中被镇压。据了解,李氏族人对其人之死并无惋惜和同情。令人遗憾的倒是历史上曾经为邻水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李征庸,因与其有养父子关系,土改时被殃及。李征庸的灵柩被挖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