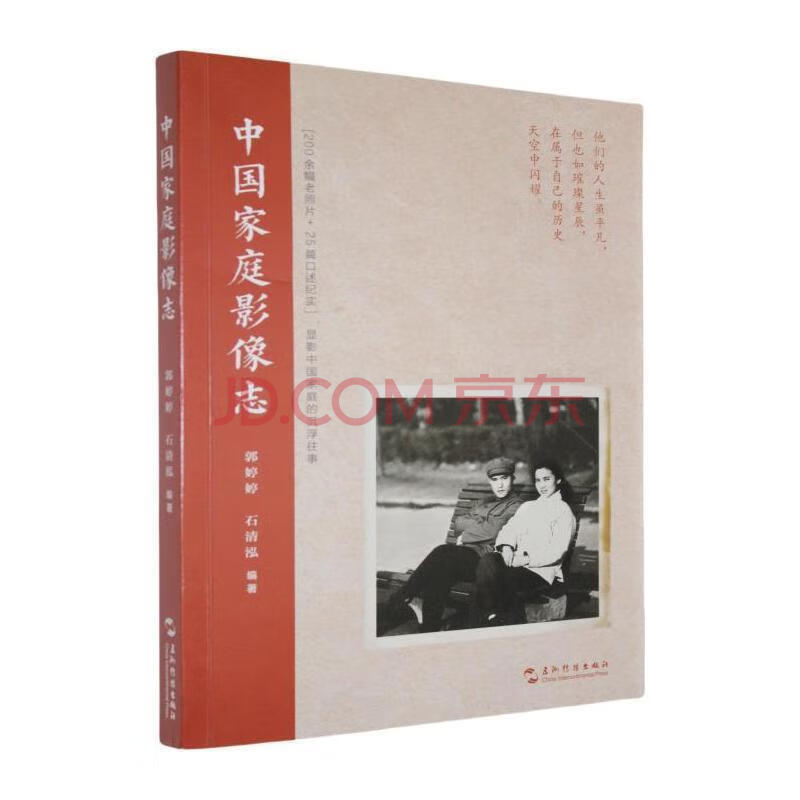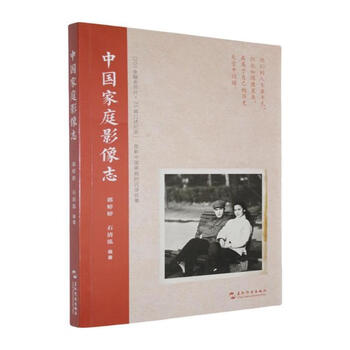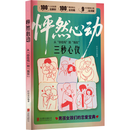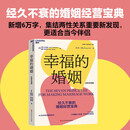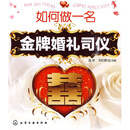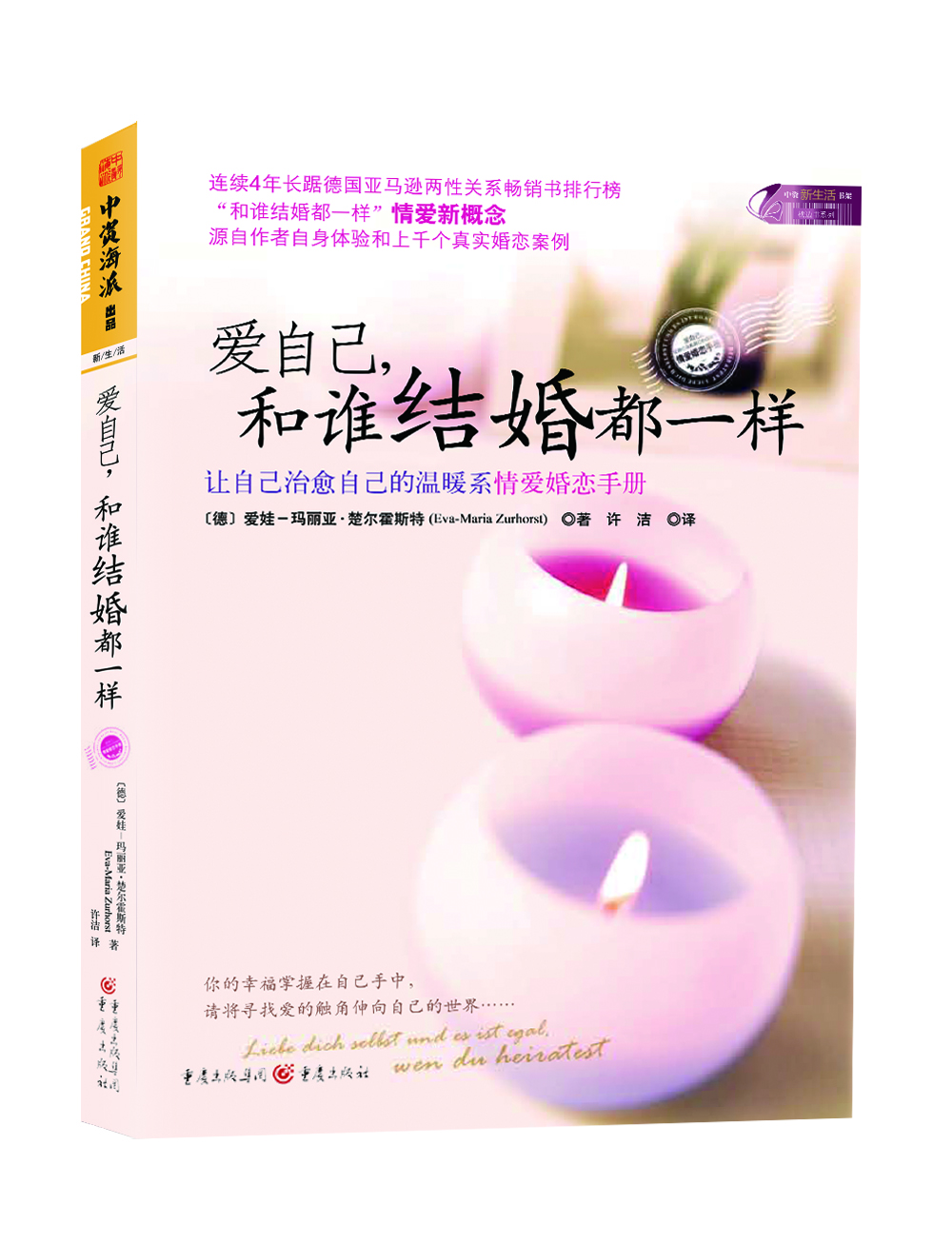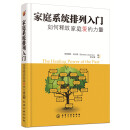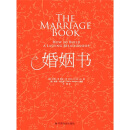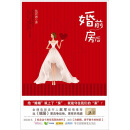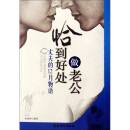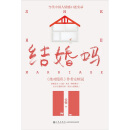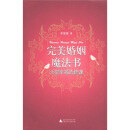内容简介
打开25个家庭珍藏的私人相册,回望父辈的人生故事。他们来自中国大江南北,身份各异,是无数个中国家庭的缩影:有百年教师之家、农村的百岁传奇老人、当年县委的“第一笔杆子”、装满整个皮箱军功章的军人,也有踏遍青山寻找铀矿的勘探队员……面对时代的动荡、命运的不公、物资的匮乏、前路的迷茫,他们依然坚韧、乐观、进取,用热气腾腾的生活,诉说人间值得。这些尘封的老照片带我们重回历史现场,展露父辈的精神气质及时代风貌,映照出社会巨变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精彩书评
书中拍摄和收集的文献
图片,历史跨度有的长达百
年。这些照片背后是一个个
漫长而扣人心弦的故事,既
是纪实,也是历史。
——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
主席 陈海汶
精彩书摘
清末民初的历史凝眸
整个家庭故事,从一张阿爷的父亲(外公的爷爷)的照片开始——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的上海南京路,照片中还留着长辫子的人正是阿爷的父亲,他是宁波镇海人。拍摄时间大概在1878年到1911年之间。当时正是民族资本家兴起的时代,阿爷的父亲在一家民族企业工作,老板对他非常和善,报酬也还算丰厚。拍这么张照片,当时应该不便宜!
当时和中国早期摄影家赖阿芳合作开办照相馆的英籍摄影师格里佛士,在给伦敦摄影新闻的一篇通讯中就描述过:在中国拍摄人像,“一定要正面对准拍摄,两耳要着得到,面部左右两边要成同样比例,双脚要安排成一样长短,比例对中国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双手也最好安排到每一根手指都清晰入相……他们要有花,桌上要放一小花瓶”。
被撕毁的平静
外公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从事汽车配件公司的会计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汽车行业公司的财务部门。
1950年12月7日,外公张惠南与外婆李美云结婚了。七十年前的新婚男女,男生要梳奶油头,女生要烫波浪头,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时尚。当时外公家里条件相当不错。家中有套房子在“文革”期间被征收,改成了一所幼儿园。那时,我外公被打成了“右派”,伤心欲绝的外婆,亲手撕掉了她和外公的结婚照。
外婆是个很时髦的女性,长年烫着头发。晚年的她痴迷足球,最喜欢皇家马德里,经常大半夜起来熬夜看球赛。在我印象中,外婆是个非常勤劳能干的人,家中落不得半点灰尘。我父亲给外婆起了个“卫生专家”的称呼。
白色恐怖时期的掩护
奶奶王新媛出生于1926年,大约20世纪30年代随家人从无锡来到上海。她天生卷发,高个子,高鼻梁、大眼睛、瓜子脸,白皮肤,像极了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
我的父亲马持平,出生于194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年。父亲的生父是国民党,在父亲七个月大的时候在外白渡桥被炸死。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对生父没有任何记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无法与马姓家族联系,家里连一张生父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尽管父亲年轻时多次试图寻找生父的家族,但一直杳无音信。
奶奶早年在白色恐怖时期掩护过地下党。那是一个夜晚,突然有两位不认识的同志,直接来敲门借宿我奶奶家,并且保证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不会过多打扰。那个时代的人,一听这番话,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奶奶没有丝毫犹豫,让这两位同志借宿了一宿。借宿者天没亮就走了。第二天白天,有人上门来找人,奶奶笃定地告诉对方,没有人来过。
新中国成立后,被掩护的地下党成员感激奶奶曾经帮助了他们,于是给她安排在上海印钞厂工作,待遇不错,奶奶一直工作到退休。
中国早期“个体户”
父亲年轻时很帅,据说当时很多女青年都在暗中议论他,给他起了个外号——“格里高利·派克”。父亲就读于上海逸夫小学和育才初中,前者由爱国人士邵逸夫建立,如今我儿子每天去上学的路上都会路过这所学校,它似乎是时间的见证者。
“文革”结束后,国家鼓励年轻人回炉考大学。当时摆在父亲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工作单位分房,可以结婚生子;一是回炉学习,重新考大学。最后父亲选择了前者。经人介绍,父亲与我母亲张建敏结婚。
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国有体制改革开始。在时代的浪潮下,父母开始下海经商、炒股。在那个时候,主流观点是在单位里工作最体面,但父母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在那个年代,放弃稳定工作下海,要承受异样的眼光,需要很大勇气。
父母在外面销售小商品,我则在家帮他们修补部分受损的商品,我的动手能力就是这个时候锻炼出来的。个体户的工作很辛苦,心理压力也很大,虽然最终父母也没赚到多少钱,但他们随时代浪潮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父母告诉我,未知世界没有那么恐怖,人生的道路无所谓好与坏,只是不同的选择而已。
爸爸是急性子,但是数学非常好,我小时候的数学都是爸爸辅导的。初三准备迎接中考的期间,我俩每天晚上一起做数学题,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宝贵时光。小时候,每逢暑假,父亲都会带我去文庙、城隍庙玩,那里有好多上海的著名小吃,如单档、双档(面筋百叶包汤),也有很多地摊售卖玩具。我们最初骑自行车去,后来买了一辆上海飞人牌助动车。我坐在前面,迎着风,爸爸蹬着车,一路前往最喜欢的地方。我们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背着妈妈偷偷出去买玩具,那时候我的玩具特别多,可以说是小朋友中数一数二的。有些玩具被我爸妈保留了下来,我儿子出生后还在玩。
妈妈属猴,性格好动。据说她从小就会拿大顶,就是用手撑地侧滚翻,我却一直学不会。我小时候,妈妈不太会做饭。有一次她想给我们爷儿俩一个惊喜,烧了一顿糖醋排骨,那口味我至今难忘——太难吃啦。我和父亲如实反馈这个菜实在难以下咽,我妈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小时候就像大小姐一样被养着的,能给你们爷俩弄点儿吃的就不错啦!”神奇的是,当有了孙子,妈妈开始
目录
序一 25个中国家庭记忆
序二 父母之爱 犹如一盏温柔的灯
第一章 史忆百年,沧海一瞬
上海滩小家庭百年变迁
棣华围的百年沧桑
从“书箱”门第到教育世家
父母的钢厂岁月
二光村的百岁传奇
人世间,六十年
杭州教师之家的百年影像
第二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风雨同行八十年
圆号吹响的流金岁月
我的“亮剑”父亲
永远青春的老爸老妈
琐碎生活的“军功章”
十字铺茶场:父辈的汗水与我的乡愁
铁血柔情:戎装岁月里的温暖守护
第三章 应有山神长守护
如青竹般蓬勃的生命
父母兵团往事
军嫂的爱,柔软亦坚强
扎根于土地的家
“乐天派”公婆的乡居岁月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第四章 乘风,拥抱堂前花
踏遍青山人未老
特殊年代的重组家庭
永远的渔夫
飞鸟的痕迹
画出人间四月天
后记 百姓家书 记录历史
试读
清末民初的历史凝眸
整个家庭故事,从一张阿爷的父亲(外公的爷爷)的照片开始——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的上海南京路,照片中还留着长辫子的人正是阿爷的父亲,他是宁波镇海人。拍摄时间大概在1878年到1911年之间。当时正是民族资本家兴起的时代,阿爷的父亲在一家民族企业工作,老板对他非常和善,报酬也还算丰厚。拍这么张照片,当时应该不便宜!
当时和中国早期摄影家赖阿芳合作开办照相馆的英籍摄影师格里佛士,在给伦敦摄影新闻的一篇通讯中就描述过:在中国拍摄人像,“一定要正面对准拍摄,两耳要着得到,面部左右两边要成同样比例,双脚要安排成一样长短,比例对中国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双手也最好安排到每一根手指都清晰入相……他们要有花,桌上要放一小花瓶”。
被撕毁的平静
外公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从事汽车配件公司的会计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汽车行业公司的财务部门。
1950年12月7日,外公张惠南与外婆李美云结婚了。七十年前的新婚男女,男生要梳奶油头,女生要烫波浪头,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时尚。当时外公家里条件相当不错。家中有套房子在“文革”期间被征收,改成了一所幼儿园。那时,我外公被打成了“右派”,伤心欲绝的外婆,亲手撕掉了她和外公的结婚照。
外婆是个很时髦的女性,长年烫着头发。晚年的她痴迷足球,最喜欢皇家马德里,经常大半夜起来熬夜看球赛。在我印象中,外婆是个非常勤劳能干的人,家中落不得半点灰尘。我父亲给外婆起了个“卫生专家”的称呼。
白色恐怖时期的掩护
奶奶王新媛出生于1926年,大约20世纪30年代随家人从无锡来到上海。她天生卷发,高个子,高鼻梁、大眼睛、瓜子脸,白皮肤,像极了那个时代的电影明星。
我的父亲马持平,出生于1948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年。父亲的生父是国民党,在父亲七个月大的时候在外白渡桥被炸死。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对生父没有任何记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无法与马姓家族联系,家里连一张生父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尽管父亲年轻时多次试图寻找生父的家族,但一直杳无音信。
奶奶早年在白色恐怖时期掩护过地下党。那是一个夜晚,突然有两位不认识的同志,直接来敲门借宿我奶奶家,并且保证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不会过多打扰。那个时代的人,一听这番话,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奶奶没有丝毫犹豫,让这两位同志借宿了一宿。借宿者天没亮就走了。第二天白天,有人上门来找人,奶奶笃定地告诉对方,没有人来过。
新中国成立后,被掩护的地下党成员感激奶奶曾经帮助了他们,于是给她安排在上海印钞厂工作,待遇不错,奶奶一直工作到退休。
中国早期“个体户”
父亲年轻时很帅,据说当时很多女青年都在暗中议论他,给他起了个外号——“格里高利·派克”。父亲就读于上海逸夫小学和育才初中,前者由爱国人士邵逸夫建立,如今我儿子每天去上学的路上都会路过这所学校,它似乎是时间的见证者。
“文革”结束后,国家鼓励年轻人回炉考大学。当时摆在父亲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工作单位分房,可以结婚生子;一是回炉学习,重新考大学。最后父亲选择了前者。经人介绍,父亲与我母亲张建敏结婚。
20世纪90年代,第一批国有体制改革开始。在时代的浪潮下,父母开始下海经商、炒股。在那个时候,主流观点是在单位里工作最体面,但父母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选择,成为中国第一批“个体户”。在那个年代,放弃稳定工作下海,要承受异样的眼光,需要很大勇气。
父母在外面销售小商品,我则在家帮他们修补部分受损的商品,我的动手能力就是这个时候锻炼出来的。个体户的工作很辛苦,心理压力也很大,虽然最终父母也没赚到多少钱,但他们随时代浪潮勇往直前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父母告诉我,未知世界没有那么恐怖,人生的道路无所谓好与坏,只是不同的选择而已。
爸爸是急性子,但是数学非常好,我小时候的数学都是爸爸辅导的。初三准备迎接中考的期间,我俩每天晚上一起做数学题,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宝贵时光。小时候,每逢暑假,父亲都会带我去文庙、城隍庙玩,那里有好多上海的著名小吃,如单档、双档(面筋百叶包汤),也有很多地摊售卖玩具。我们最初骑自行车去,后来买了一辆上海飞人牌助动车。我坐在前面,迎着风,爸爸蹬着车,一路前往最喜欢的地方。我们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背着妈妈偷偷出去买玩具,那时候我的玩具特别多,可以说是小朋友中数一数二的。有些玩具被我爸妈保留了下来,我儿子出生后还在玩。
妈妈属猴,性格好动。据说她从小就会拿大顶,就是用手撑地侧滚翻,我却一直学不会。我小时候,妈妈不太会做饭。有一次她想给我们爷儿俩一个惊喜,烧了一顿糖醋排骨,那口味我至今难忘——太难吃啦。我和父亲如实反馈这个菜实在难以下咽,我妈却理直气壮地说:“我小时候就像大小姐一样被养着的,能给你们爷俩弄点儿吃的就不错啦!”神奇的是,当有了孙子,妈妈开始
前言/序言
25个中国家庭记忆 生活的感知是复杂的, 摄影的呈现和表达是多元的 。但我相信,我们对摄影最 初的认识都是从与家人的合 影和肖像照开始的,这是摄 影原始的意义。用我们手中 的相机,以最朴素的方式, 为自己的情感做一些记录,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我翻开手中这本《中 国家庭影像志》,我惊诧于 如此大面积、多维度、力透 纸背的家族历史故事,图文 并茂地展现眼前。大江南北 ,有这么多摄影人跟我一样 ,愿意用相机记录身边的日 常,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和 对亲人最诚挚的爱,也为社 会历史研究留下一些线索和 记忆。 优秀的纪实图片是有灵 魂的。《中国家庭影像志》 收集和拍摄的文献图片,历 史跨度有的长达百年。几十 年前,拍照是件很有仪式感 的大事。图片所提供的都是 最能表达当时情境的信息, 每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扣人 心弦的故事。这些,是纪实 ,更是历史。 读25个家庭记忆的故事 ,令我触景生情,好像在故 事中看到了自己。我从小生 活在上海的一个下只角(平 民生活区域),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温情而拮据的生 活贯穿了我的童年,也让我 养成了性格中最重要的底色 ——平民视角。我的拍摄方 向,很多来自家庭这个情感 源头。 我的父亲是浙江上虞人 。1949年,父亲为了逃避 抓壮丁,带着家人逃到上海 谋生。刚开始,父亲帮人拉 两轮搭车搞运输,新中国成 立后被收编到国有工厂,成 为一名车工,后来父亲因技 术革新还上过报纸,经常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小时候, 我们家居住的狭小的亭子间 里,父亲的大摞奖状,多得 无处安放。 1966年,我8岁,父亲为 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 为人民”的号召,前往安徽 泾县683基地支援“三线建设 ”十年有余。父亲任劳任怨 一辈子,60岁退休那天,挤 公交车没挤上,跌了一跤, 脑袋撞在马路牙子上,从此 一边瘫。退休的好日子一天 没享受过,没几年父亲就走 了,这份痛,一直扎在我的 心里。与父亲情感上的断联 ,我无力挽回。为了纪念父 亲,我决定做黄浦江两岸, 包括上海老工业题材的拍摄 。 2000年到2006年,我在 空中飞了100多小时,一家 一家找,跑遍黄浦江两岸的 2000多家钢铁厂、造船厂 、修船厂、码头。通过查找 资料,弄清楚这些工厂什么 时候开始建的,什么时候倒 的,什么时候改变的,百万 产业工人下岗如何悄悄淹没 在人海之中。临走前,从工 人们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 了父亲。如果我的照片能还 给他们尊严,能替他们倾诉 时代的声音,能把那个时代 曾经的表情记录下来,让后 人向他们致敬,我想作为摄 影人我的工作算是完成了, 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因此,我特别理解本书 的策划人郭婷婷女士,以及 25位摄影师的心情和创作动 机,从情感、历史研究、摄 影师的本职来说,撰写和制 作此书都是很有意义的,感 谢他们的坚持和努力,给读 者呈现如此复杂漫长而又短 暂的人类瞬间。 陈海汶 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主 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