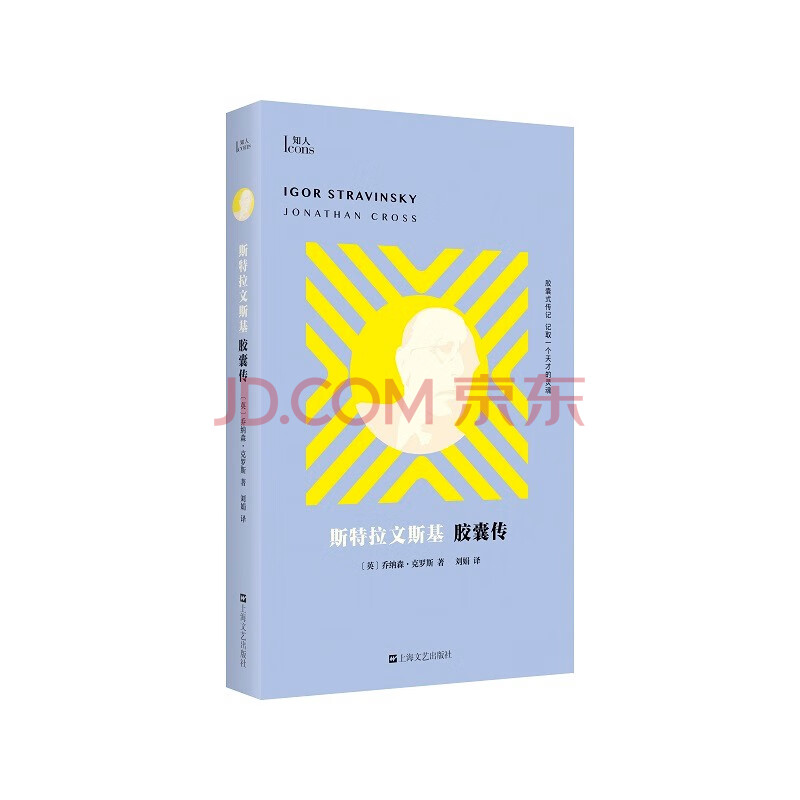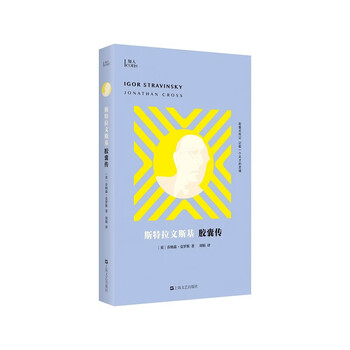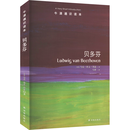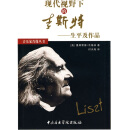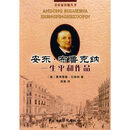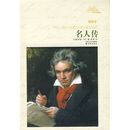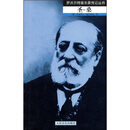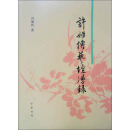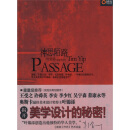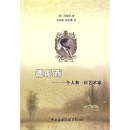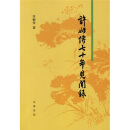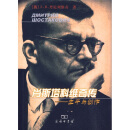内容简介
就像俄罗斯娃娃“玛特廖什卡”,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诞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的一生只是动荡时代背景的缩影。他的音乐以精妙而复杂的方式记录了他的一生。也许我们无法找到原真的斯特拉文斯基。也许“斯特拉文斯基”只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一项发明。但是,这项发明本身就是一个时代和地点的产物。
英国牛津大学音乐学教授、斯特拉文斯基专家乔纳森·克罗斯带领我们寻找斯特拉文斯基其人、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艺术之间的关联,力图揭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如何以及为何如此强有力地反映了它所处的时代。
精彩书评
斯特拉文斯基是我心中的乐神,他一直是我作为一个音乐家的励志与创作的榜样。但我真正开始从智慧和信仰的层面,深刻地认识他、理解他,那是在我指挥了他的《春之祭》《火鸟》《夜莺》及《焰火》之后的事,因为那时我没有遇到一本伟大而有趣的书,能够从生平与故事、信仰与智慧、历史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等方面,生动、深刻地介绍他,所以我仅能从他的音乐总谱里去寻觅那个神秘而又迷人的音乐之灵。嘿,等了这么多年,这本书终于出现了,当我读到刘娟翻译的《斯特拉文斯基胶囊传》时,它让我爱不释手,觉得它有时像是电影,有时像是诗,有时它更像是带着我在秘境中与这位可爱、固执、自由、浪荡的现代音乐之神,有着穿越式的、沉浸式的接触与碰撞。无论你是舞者、文艺青年、作曲家或指挥、建筑师或诗人、自然与自由之人,这本书可以为你带来智慧与信仰,执着与浪漫的人生思考,更会诱发你对神秘与幽野的大自然,有着无限的迷恋。
——谭盾 2025年7月15日于水乐堂
(作曲家,指挥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亲善大使)
斯特拉文斯基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和最重要的音乐巨匠之一,对于现代音乐的发展意义重大。此书秉持现代学术精神,以批判性眼光和清晰的笔触,全面展现这位具有“世界公民”色彩的俄罗斯作曲家复杂而多面的人生,并对其重要代表作作出中肯分析和评价,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特此大力推荐!
——杨燕迪(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会长)
英国牛津大学的乔纳森·克罗斯教授是当代资深的斯特拉文斯基研究学者,编辑出版过多部相关著作。这本由剑桥大学在读博士刘娟翻译的新作,属于经典的“大家小书”类型:文字书写浅显易懂、妙趣横生,思考与诠释却独到深刻、入木三分。克罗斯以一种反思与批判的视角,将斯特拉文斯基从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叙事中解脱出来,并置于多维变动的时代与文化语境中重新加以解读。他在主人公刻意寻求的秩序与规则的面具之下,体认到一个动荡的、充满个人悲剧的时代。这本评传将彻底动摇我们对于这位20世纪伟大作曲家的固有认知,重新了解其与俄罗斯民间文化及东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深刻联系,了解其在圣彼得堡、巴黎和新大陆的社交圈,其新古典主义音乐与同时代装饰艺术风格的相似性,以及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流亡境遇如何形塑了他的思想与音乐。
打开名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层层套娃,窥得“伊戈尔”的面目——斯特拉文斯基权威研究者乔纳森·克罗斯将作曲家的个人经历与音乐发展巧妙地交织一体,揭示出漂泊生涯与文化语境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本语言精练清晰、译笔风格流畅的传记将让读者从新的视角理解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和生活。
——何弦(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
精彩书摘
斯特拉文斯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上的熟人往往对他的外表印象深刻,还会在信件和日记里记录这一点。一些报纸经常会评论他的着装选择。1920年代中期,侄女塔尼娅(Tanya)在斯特拉文斯基家中住了将近一年,她是叔叔衣柜的热心记录者。在给父母的信中,她写道:“他着装亮眼,有很多领带。”1924年,让·科克托给斯特拉文斯基的许多时髦配饰编了号,但他也很快意识到,这些只是他外表世界的一部分:
戒指、绑腿、围巾、半腰带、领带、领带夹、腕表、厚围巾、护身符、夹鼻眼镜[原文如此]、单片眼镜、眼镜、链式手镯,都无法充分传达他的面貌。简单来讲,它们表明,从外在上来看,斯特拉文斯基无意讨好任何人。他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想怎么装扮就怎么装扮,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它们或许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不同的画像同样表明斯特拉文斯基有多在乎以时兴的方式穿戴。部分原因可能是受恐惧驱使,他害怕被当作乡巴佬,害怕显得与战后见多识广的巴黎社会格格不入。这种感觉同样是他的音乐在1920年代偏离俄罗斯,转而与西欧音乐经典站在同一阵线的原因。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在着装审美和音乐方面都是,而且他最渴求的是被当成一个现代人。
斯特拉文斯基对于自我和身体的狂热,强化了他自孩童时期以来对自己健康问题的执着。与母亲一样,他是一位疑病症患者。他的一生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春之祭》首演之后,他显然是吃了一只坏掉的牡蛎感染了伤寒症。仅在四年之后,这个病就要了他弟弟古里的命。医疗账单和谁来支付这些账单是他信件里不断出现的主题。但是,他无法控制对于香烟、美酒和佳肴的喜爱。这些都是成为名流圈一份子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在圣彼得堡已经对夜店产生了浓厚兴趣。正是在巴黎的这些场所,他见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喜欢与这位知名作曲家作伴,这些人反过来也对他最有帮助。1920年,《普尔钦奈拉》在巴黎歌剧院成功首演,紧随其后的纵酒狂欢只是他参加过的许多狂野社交之夜中的一次。尽管言人人殊,但佳吉列夫可能就是在这种特殊场合向斯特拉文斯基引见了“可可”加布里埃尔·香奈儿。
香烟是斯特拉文斯基对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使用的是一支长且线条柔和的烟嘴。西奥多记得父亲这样告诉家人:“它是由信天翁的喙制成”,“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斯特拉文斯基频繁与它一起出镜。与飞来波女郎和汽车一样,香烟也象征着一种令人向往的战后自由主义潮流。在香烟不断将市场瞄准女性,以及女性开始抽烟之后,更是如此。又一次,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讲,自己是否被视作这个现代社会的一分子,至关重要。他的着装和举止是他融入这种环境的一部分。1910年,巴黎在《火鸟》首演那晚爱上了斯特拉文斯基,而斯特拉文斯基也爱上了巴黎。从那时起,直到他1939年动身去美国定居,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功都与“光明之城”巴黎的生活密切关联。
[……]
在战后时尚革命的领军人物中,香奈儿最为出色。作为斯特拉文斯基1920年那段婚外情的对象,她走进了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这段关系虽然引起过诸多猜疑,也不可避免地被夸大,还是一部成功小说和电影的主线,但这段绯闻并没有在传闻之外得到任何确凿证据的支持。直到1946年,香奈儿才向保罗·莫朗坦白。而直到30年之后,可可和伊戈尔都已经去世,莫朗才将香奈儿的坦白公之于众。无论如何,看起来,香奈儿与斯特拉文斯基一样,都十分擅长重塑自己的过往。尽管如此,鉴于当事双方的脾性,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二人之间的强大吸引力。就像丹尼丝·斯特拉文斯基在得到丈夫西奥多许可后所说:“伊戈尔轻浮,香奈儿勾人。”1920年秋天,香奈儿邀请一贫如洗的斯特拉文斯基一家及随行人员搬离布列塔尼(在战争期间长期逗留瑞士之后,他们刚搬到这里),让他们住进了她在巴黎西郊加尔什新购置的新艺术风格别墅“绿色气息”(Bel Respiro)。(香奈儿自己住在旺多姆广场利兹酒店豪华套房。)她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仰慕者。1913年,在《春之祭》预演时,她第一次听到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如今,她捐赠了一大笔钱,让佳吉列夫得以上演由马西涅编舞的新制作。据传,作曲家在“绿色气息”安顿下来后不久,这段婚外情就开始了。长远来看,这样一种情况不可持续。因此,到了第二年春天,这家人就以凯瑟琳身体虚弱为借口,搬往了比亚里茨。无疑,比亚里茨是一个时髦地方,而且是香奈儿1905年开业的第二间店铺所在地。这个地方虽然仍在法国境内,但是距离巴黎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普莱耶尔钢琴公司提供的一间位于罗什舒瓦尔街厂房楼上的工作室成了斯特拉文斯基在首都的新落脚点。音乐、工作和婚外情,如今可以远离家人的凝视,安全进行。但是,他跟自己起了冲突。不论他在巴黎待多久,他总是称凯瑟琳和家人所在之处为“我家”。
在斯特拉文斯基见到并疯狂爱上后来的情妇
目录
前言:寻找伊戈尔
序章:斯特拉文斯基如何成了“斯特拉文斯基”
1. 圣彼得堡之子
2. 俄罗斯芭蕾
3. 丑闻画像
4. 第一次流亡:瑞士、战争与革命
5. 一次与创作有关的顿悟:巴黎风格和新古典主义
6. 荣耀归于神
7. 一段非比寻常的创作合伙关系:斯特拉文斯基与巴兰钦
8. 另一场战争,另一个国家
9. 一部与歌剧有关的歌剧
10. 危机与出路
11. 一位现代世界公民
终章:斯特拉文斯基仍在
部分参考文献
部分唱片和影像作品目录
致谢
图片致谢
试读
斯特拉文斯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上的熟人往往对他的外表印象深刻,还会在信件和日记里记录这一点。一些报纸经常会评论他的着装选择。1920年代中期,侄女塔尼娅(Tanya)在斯特拉文斯基家中住了将近一年,她是叔叔衣柜的热心记录者。在给父母的信中,她写道:“他着装亮眼,有很多领带。”1924年,让·科克托给斯特拉文斯基的许多时髦配饰编了号,但他也很快意识到,这些只是他外表世界的一部分:
戒指、绑腿、围巾、半腰带、领带、领带夹、腕表、厚围巾、护身符、夹鼻眼镜[原文如此]、单片眼镜、眼镜、链式手镯,都无法充分传达他的面貌。简单来讲,它们表明,从外在上来看,斯特拉文斯基无意讨好任何人。他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想怎么装扮就怎么装扮,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它们或许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不同的画像同样表明斯特拉文斯基有多在乎以时兴的方式穿戴。部分原因可能是受恐惧驱使,他害怕被当作乡巴佬,害怕显得与战后见多识广的巴黎社会格格不入。这种感觉同样是他的音乐在1920年代偏离俄罗斯,转而与西欧音乐经典站在同一阵线的原因。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在着装审美和音乐方面都是,而且他最渴求的是被当成一个现代人。
斯特拉文斯基对于自我和身体的狂热,强化了他自孩童时期以来对自己健康问题的执着。与母亲一样,他是一位疑病症患者。他的一生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但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春之祭》首演之后,他显然是吃了一只坏掉的牡蛎感染了伤寒症。仅在四年之后,这个病就要了他弟弟古里的命。医疗账单和谁来支付这些账单是他信件里不断出现的主题。但是,他无法控制对于香烟、美酒和佳肴的喜爱。这些都是成为名流圈一份子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在圣彼得堡已经对夜店产生了浓厚兴趣。正是在巴黎的这些场所,他见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喜欢与这位知名作曲家作伴,这些人反过来也对他最有帮助。1920年,《普尔钦奈拉》在巴黎歌剧院成功首演,紧随其后的纵酒狂欢只是他参加过的许多狂野社交之夜中的一次。尽管言人人殊,但佳吉列夫可能就是在这种特殊场合向斯特拉文斯基引见了“可可”加布里埃尔·香奈儿。
香烟是斯特拉文斯基对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使用的是一支长且线条柔和的烟嘴。西奥多记得父亲这样告诉家人:“它是由信天翁的喙制成”,“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斯特拉文斯基频繁与它一起出镜。与飞来波女郎和汽车一样,香烟也象征着一种令人向往的战后自由主义潮流。在香烟不断将市场瞄准女性,以及女性开始抽烟之后,更是如此。又一次,对于斯特拉文斯基来讲,自己是否被视作这个现代社会的一分子,至关重要。他的着装和举止是他融入这种环境的一部分。1910年,巴黎在《火鸟》首演那晚爱上了斯特拉文斯基,而斯特拉文斯基也爱上了巴黎。从那时起,直到他1939年动身去美国定居,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功都与“光明之城”巴黎的生活密切关联。
[……]
在战后时尚革命的领军人物中,香奈儿最为出色。作为斯特拉文斯基1920年那段婚外情的对象,她走进了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这段关系虽然引起过诸多猜疑,也不可避免地被夸大,还是一部成功小说和电影的主线,但这段绯闻并没有在传闻之外得到任何确凿证据的支持。直到1946年,香奈儿才向保罗·莫朗坦白。而直到30年之后,可可和伊戈尔都已经去世,莫朗才将香奈儿的坦白公之于众。无论如何,看起来,香奈儿与斯特拉文斯基一样,都十分擅长重塑自己的过往。尽管如此,鉴于当事双方的脾性,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二人之间的强大吸引力。就像丹尼丝·斯特拉文斯基在得到丈夫西奥多许可后所说:“伊戈尔轻浮,香奈儿勾人。”1920年秋天,香奈儿邀请一贫如洗的斯特拉文斯基一家及随行人员搬离布列塔尼(在战争期间长期逗留瑞士之后,他们刚搬到这里),让他们住进了她在巴黎西郊加尔什新购置的新艺术风格别墅“绿色气息”(Bel Respiro)。(香奈儿自己住在旺多姆广场利兹酒店豪华套房。)她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仰慕者。1913年,在《春之祭》预演时,她第一次听到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如今,她捐赠了一大笔钱,让佳吉列夫得以上演由马西涅编舞的新制作。据传,作曲家在“绿色气息”安顿下来后不久,这段婚外情就开始了。长远来看,这样一种情况不可持续。因此,到了第二年春天,这家人就以凯瑟琳身体虚弱为借口,搬往了比亚里茨。无疑,比亚里茨是一个时髦地方,而且是香奈儿1905年开业的第二间店铺所在地。这个地方虽然仍在法国境内,但是距离巴黎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普莱耶尔钢琴公司提供的一间位于罗什舒瓦尔街厂房楼上的工作室成了斯特拉文斯基在首都的新落脚点。音乐、工作和婚外情,如今可以远离家人的凝视,安全进行。但是,他跟自己起了冲突。不论他在巴黎待多久,他总是称凯瑟琳和家人所在之处为“我家”。
在斯特拉文斯基见到并疯狂爱上后来的情妇
前言/序言
◎ 绪论
想一个象征着俄罗斯、俄罗斯人的符号。首先映入脑海的会是什么?最有可能的是一个木制娃娃,它嵌套在尺寸逐渐递增的许多其他木制娃娃内,被装饰成一个乡村女孩或妇女,有着黑色的眼睛和勾画分明的睫毛、玫瑰色的红脸颊。她总是戴着头巾,身着缀有鲜艳花朵的围裙。这就是玛特廖什卡——俄罗斯套娃。玛特廖娜或玛特里奥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名字。这个词的词根是拉丁语mater,与现代俄语中“母亲”一词相关。因而,对于俄罗斯人而言,玛特廖什卡便被亲切地与母亲和母性形象关联了起来,并由此与俄罗斯祖国这一概念相关。植根于一个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的古老民族的技艺和传统,这些小木娃娃代表着一种不朽的罗斯理念。于外人而言,玛特廖什卡娃娃也通常被认为象征着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俄罗斯精神。用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爆发时的一句名言来说,俄罗斯“是一个谜团里头的谜题裹着的谜语”。
在俄罗斯,木工有着悠久传统,这一点毋庸置疑。谢尔盖耶夫镇是一个著名的民间艺术中心,它位于莫斯科以北约70公里。“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在13世纪制作了谢尔盖耶夫镇的第一个玩具……沙皇的孩子们早在1628年就收到过来自谢尔盖耶夫镇的玩具……[到了]1880年,谢尔盖耶夫镇坐拥322家玩具作坊”。但是,这其中没有玛特廖什卡。如今著名的玛特廖什卡娃娃直到1899年才首次出现在谢尔盖耶夫镇。嵌套娃娃的理念实际上是从日本进口。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个俄罗斯玛特廖什卡娃娃是在阿布拉姆采沃艺术村中绘制而成,那是一个是由富裕的铁路大亨萨瓦·马蒙托夫和妻子伊丽莎白在谢尔盖耶夫镇外不远的庄园中建立起来的艺术家聚集地。阿布拉姆采沃成了一个艺术、歌剧大熔炉,在此酝酿着一种俄罗斯新民族主义美学。玛特廖什卡虽然植根于农民手工艺品,但是它诞生自一种既贵族又现代的渴望,即保存迅速消逝的过去,并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俄罗斯这一理念。1900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一件玛特廖什卡娃娃样品与其他俄罗斯民间艺术品一起展出,自此成为抢手的国际商品。在它斩获奖项后,订单开始迅速涌入,让一代又一代俄罗斯工匠保住了饭碗。在这场展览上,有一位看到这个娃娃的俄罗斯游客,名叫谢尔盖·佳吉列夫。这不禁让他思考,在巴黎,人们对于进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俄罗斯物件的热情,或许延伸到了大宗生产的木制小雕像之外。
事实证明,那些西方确信是古老俄罗斯民间精神的原真体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新发明,其推手是现代性的两大双生子:怀旧和商业。
1898年,就是玛特廖什卡出现的前一年,在佳吉列夫的领导下,一群富裕、年轻的圣彼得堡艺术家和思想家在“艺术世界”的旗帜下首次公开惊艳亮相。“艺术世界”既是一本杂志,也是一项运动,专注于以激进的方式呈现一种源自民间传统的新俄罗斯艺术。其中有些人甚至与阿布拉姆采沃有过接触。事实证明,他们对于早期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具有决定意义。不出十年,斯特拉文斯基及其合作者们就会取用旧俄的一些故事、艺术和音乐,令它们脱胎换骨,变成一部出口巴黎的芭蕾。法国人喜爱火鸟的魅力、色彩和被发明的原真性。他们欣然接受它,就像接受玛特廖什卡一样。他们也欣然接受了后来把法国当成了家乡且将自己重新打造成法国人的斯特拉文斯基。为了迎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局势,他在音乐中展现出一种新的法式姿态。几十年后,为了呈现一位美式斯特拉文斯基,这个“娃娃”被再一次拧开拆散。为了表示对东道主的敬重,他会说起另一门新语言。
为自我重塑大师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作传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确实,得益于一批杰出学者孜孜不倦的工作,与他一生相关的诸多事实和行为习惯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他们毕生致力于研究满是信函、日记、手稿、合同、医疗和法律账单的档案,以及其他大量相关材料;他们搜寻证据以确认或是反驳由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家人、支持者和辩护者公开发表的言论。然而,许多未知事物、不确定因素和矛盾仍然存在。即便那些非常熟悉斯特拉文斯基的人(在世或离世)的证言也不值得完全信任,因为他们讲述的一些故事前后并不一致。所以,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真正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呢?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怎么才能认出他?
就像玛特廖什卡,斯特拉文斯基诞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在他有生之年,他出生时的国家变得几乎无法辨认。作为一位流亡者,斯特拉文斯基主要从远处观察着这种变化,但战争与革命、疾病与死亡仍然留下了伤口。他鲜少谈论这些事情。但是,伤口无疑就在那里,它们可以在他创作的音乐中被听见。就像玛特廖什卡,他的艺术诞生自怀旧之情,这是对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俄罗斯的怀念,对一个也许是想象中的俄罗斯的怀念。但是,这是一个形塑了他的俄罗斯,是一个他出于现代目的而转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