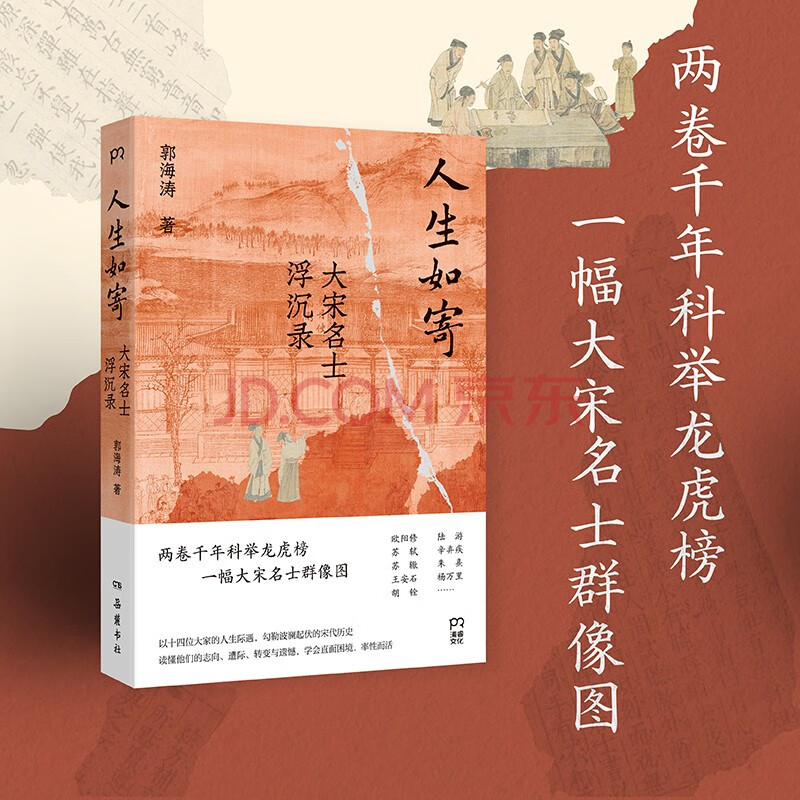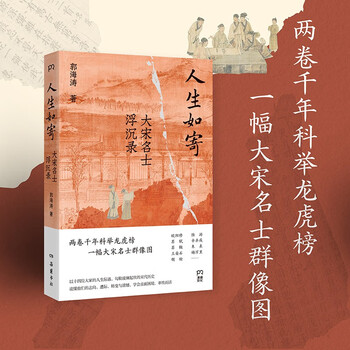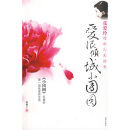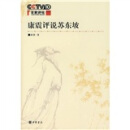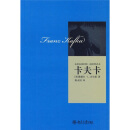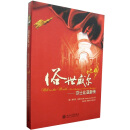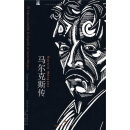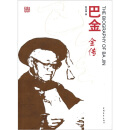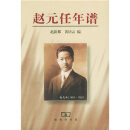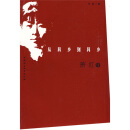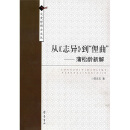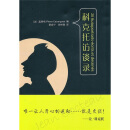内容简介
宋朝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涌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才子名臣。在选录人才的科举考试中,两宋各诞生了一卷“千年龙虎榜”:北宋嘉佑二年进士榜和南宋绍兴二十四年进士榜。本书以这两次科举名榜为引子,讲述了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十四位文豪、名士的真实人生,有奋斗的艰辛,有怀才不遇的愁苦,有人生浮沉的感慨……借由这些千古名士的雪泥鸿爪之迹,看见宋朝的清明盛世及其背后潜伏的危机,也在他们的故事中观照己身,学会直面困境,率性而活。
精彩书摘
嘉祐二年科举:千年第一龙虎榜(节选)
1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这是欧阳修于嘉祐二年(1057)知礼部贡举时的诗作,也是那次省考的珍贵快照。
初春的东京汴梁,岸柳初萌,春气渐暖,院门紧锁的礼部贡院内则是一种肃穆紧张的考试气氛。置身于数千张青涩而朝气蓬勃的面孔间,欧阳修忍不住感慨自己垂垂老矣。庆历年间,他与余靖、蔡襄、王素三人一同任谏官,他们血气方刚、直言敢谏,被人视为“一棚鹘”。历经二十年世事风雨的磨炼,他这只鹘已然褪去当年的桀骜和狂妄,演变为一只成熟的猎鹰。虽然廓清天下的大目标遥不可及,但作为科举主考官,改变当世文风,为国家选拔一批真正务实的才俊,还是应该容易实现的。
经过范仲淹、欧阳修推动的庆历兴学改革,宋初典丽浮艳的弱质文风得以纠正,但是没想到过犹不及,现在的文风走入险怪迂阔一路,“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言论偏激、脱离实际,语言晦涩、怪诞,用典生僻。举两句为例:“狼子豹孙,林林逐逐”,“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粗暴、诡异的文字组合,像不像人工智能软件写的文章?
对于欧阳修而言,这一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此前,许多礼部奏名进士屡屡倒在殿试这最后一关。“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王栐《燕翼诒谋录》)对于那些苦读数十年、命运不济的考生而言,自杀绝不是唯一的选择。秉承“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把自己制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的原则,有一个叫张元的落第考生剑走偏锋,毅然决然地做了汉奸,到西夏李元昊那里做了狗头军师,给大宋制造了大大的麻烦。受此刺激,朝廷启动了嘉祐二年的殿试改革,给后来无数的士子带来了福音。坏消息是,当年参加科举的士子里,有许多他熟悉的面孔:弟子曾巩、王回、王向……还有刚认识的苏轼、苏辙。欧阳修简直要犯选择困难症了。
2
苏洵父子三人是嘉祐元年(1056)五月抵京的。这么早早来京,是因为苏轼兄弟没有参加老家益州的解试,必须通过汴京的解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类似异地高考。他们在汴京的日子估计很难熬,当年五月至秋京师大水,当时又没有海绵城市的概念,汴京城被淹得一片狼藉。贵为枢密使(国防部部长)的狄青都只能全家住在相国寺的大殿上,欧阳修晚上只能住在筏子上,苏洵父子三人在京城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兄弟俩很争气,顺利通过了景德寺“秋试”(汴京解试)。根据当年的大数据分析,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子有四十万人,最后有资格参加省试的仅四千七百多人,是真正的百里挑一。嘉祐二年(1057),眉山籍共四十五人参加解试,最后获得省试资格的有十三人,眉山也算是人杰地灵之处。
苏家兄弟忙着备考,老爸苏洵也不闲着。他频频上书:《上文丞相书》《上富丞相书》《上韩枢密书》《上王长安书》……把当朝执政和显要拜谒了个遍。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他的长处。早年被科举虐得失去自尊和理想,又长年僻居西蜀,苏老泉在朝廷里基本没有什么人脉。但可怜天下父母心,苏洵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苏老泉颇似晚唐杜牧,一直以兵家自许,有《权书》《几策》等战争学著作,且很有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派,现在恰好实践一下。他写给韩琦的信,画风是这样的:“老兄,我觉得你的管理太佛系了。对于那些丘八(“兵”字的拆分),应该多杀几个来祭旗,坚决一点,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他右手拍着人家肩膀,左手做出一个砍杀的手势。外人听着,还以为两人是多年的铁哥们,其实只是交浅言深。可以想象一下韩琦当时脸上礼貌而不失尴尬的表情。干谒结果无疑很悲剧:“(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叶梦得《避暑录话》)
苏老泉与欧阳修的见面也很尴尬。苏洵信心满满地奉上雷简夫和张方平的推荐信,这两人都是苏家父子的伯乐。知雅州的雷简夫读了老苏文,感觉相见恨晚,由此结识苏洵父子三人,热心的他又将三苏推荐给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苏老泉事先肯定没有做过功课,不知道雷简夫与欧阳修仅仅是点头之交,而张方平更是欧阳修的政敌。好在结局非常圆满,欧阳修是以道会友之人,喜欢上了苏老泉的纵横家做派。当年十二月,真正的后援张方平恰好从益州入京调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父子赶往开封西百里外的郑州去迎接。“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苏洵《上张侍郎第二书》)接任张方平的是宋祁,就是那位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名满天下的“红杏尚书”,随从数百人威风凛凛地从东而来,苏洵父子三人不得不在冰天雪地里给他们
目录
北宋篇
嘉祐二年科举:千年第一龙虎榜
欧阳修与苏轼:跨越三十年的合奏
苏轼:峨眉山上吹下的风
王安石:退隐半山园
曾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苏辙:不只是哥哥的小迷弟
章惇:我就是那个穷凶极恶之人
状元郎:功业便从今日去,莫教人道只文章
南宋篇
绍兴二十四年科举:破碎山河下的赤子热血
胡铨:秦桧最痛恨的人
陆游、辛弃疾:南宋双子星
朱熹:
我可不是个古板的老夫子
虞允文:采石矶上的千古名
杨万里:只凭一身浩然气,完成人生逆袭
韩元吉:一个正史无名的大家
姜夔:也许卑微,但绝不悲惨
试读
嘉祐二年科举:千年第一龙虎榜(节选)
1
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
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这是欧阳修于嘉祐二年(1057)知礼部贡举时的诗作,也是那次省考的珍贵快照。
初春的东京汴梁,岸柳初萌,春气渐暖,院门紧锁的礼部贡院内则是一种肃穆紧张的考试气氛。置身于数千张青涩而朝气蓬勃的面孔间,欧阳修忍不住感慨自己垂垂老矣。庆历年间,他与余靖、蔡襄、王素三人一同任谏官,他们血气方刚、直言敢谏,被人视为“一棚鹘”。历经二十年世事风雨的磨炼,他这只鹘已然褪去当年的桀骜和狂妄,演变为一只成熟的猎鹰。虽然廓清天下的大目标遥不可及,但作为科举主考官,改变当世文风,为国家选拔一批真正务实的才俊,还是应该容易实现的。
经过范仲淹、欧阳修推动的庆历兴学改革,宋初典丽浮艳的弱质文风得以纠正,但是没想到过犹不及,现在的文风走入险怪迂阔一路,“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言论偏激、脱离实际,语言晦涩、怪诞,用典生僻。举两句为例:“狼子豹孙,林林逐逐”,“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粗暴、诡异的文字组合,像不像人工智能软件写的文章?
对于欧阳修而言,这一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此前,许多礼部奏名进士屡屡倒在殿试这最后一关。“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摒弃于殿试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王栐《燕翼诒谋录》)对于那些苦读数十年、命运不济的考生而言,自杀绝不是唯一的选择。秉承“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把自己制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的原则,有一个叫张元的落第考生剑走偏锋,毅然决然地做了汉奸,到西夏李元昊那里做了狗头军师,给大宋制造了大大的麻烦。受此刺激,朝廷启动了嘉祐二年的殿试改革,给后来无数的士子带来了福音。坏消息是,当年参加科举的士子里,有许多他熟悉的面孔:弟子曾巩、王回、王向……还有刚认识的苏轼、苏辙。欧阳修简直要犯选择困难症了。
2
苏洵父子三人是嘉祐元年(1056)五月抵京的。这么早早来京,是因为苏轼兄弟没有参加老家益州的解试,必须通过汴京的解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类似异地高考。他们在汴京的日子估计很难熬,当年五月至秋京师大水,当时又没有海绵城市的概念,汴京城被淹得一片狼藉。贵为枢密使(国防部部长)的狄青都只能全家住在相国寺的大殿上,欧阳修晚上只能住在筏子上,苏洵父子三人在京城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兄弟俩很争气,顺利通过了景德寺“秋试”(汴京解试)。根据当年的大数据分析,全国参加解试的士子有四十万人,最后有资格参加省试的仅四千七百多人,是真正的百里挑一。嘉祐二年(1057),眉山籍共四十五人参加解试,最后获得省试资格的有十三人,眉山也算是人杰地灵之处。
苏家兄弟忙着备考,老爸苏洵也不闲着。他频频上书:《上文丞相书》《上富丞相书》《上韩枢密书》《上王长安书》……把当朝执政和显要拜谒了个遍。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也不是他的长处。早年被科举虐得失去自尊和理想,又长年僻居西蜀,苏老泉在朝廷里基本没有什么人脉。但可怜天下父母心,苏洵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苏老泉颇似晚唐杜牧,一直以兵家自许,有《权书》《几策》等战争学著作,且很有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派,现在恰好实践一下。他写给韩琦的信,画风是这样的:“老兄,我觉得你的管理太佛系了。对于那些丘八(“兵”字的拆分),应该多杀几个来祭旗,坚决一点,让他们知道你的厉害。”他右手拍着人家肩膀,左手做出一个砍杀的手势。外人听着,还以为两人是多年的铁哥们,其实只是交浅言深。可以想象一下韩琦当时脸上礼貌而不失尴尬的表情。干谒结果无疑很悲剧:“(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叶梦得《避暑录话》)
苏老泉与欧阳修的见面也很尴尬。苏洵信心满满地奉上雷简夫和张方平的推荐信,这两人都是苏家父子的伯乐。知雅州的雷简夫读了老苏文,感觉相见恨晚,由此结识苏洵父子三人,热心的他又将三苏推荐给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苏老泉事先肯定没有做过功课,不知道雷简夫与欧阳修仅仅是点头之交,而张方平更是欧阳修的政敌。好在结局非常圆满,欧阳修是以道会友之人,喜欢上了苏老泉的纵横家做派。当年十二月,真正的后援张方平恰好从益州入京调任三司使(财政部部长),父子赶往开封西百里外的郑州去迎接。“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有导骑从东来,惊愕下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从者数百人,足声如雷,已过,乃敢上马徐去。”(苏洵《上张侍郎第二书》)接任张方平的是宋祁,就是那位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名满天下的“红杏尚书”,随从数百人威风凛凛地从东而来,苏洵父子三人不得不在冰天雪地里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