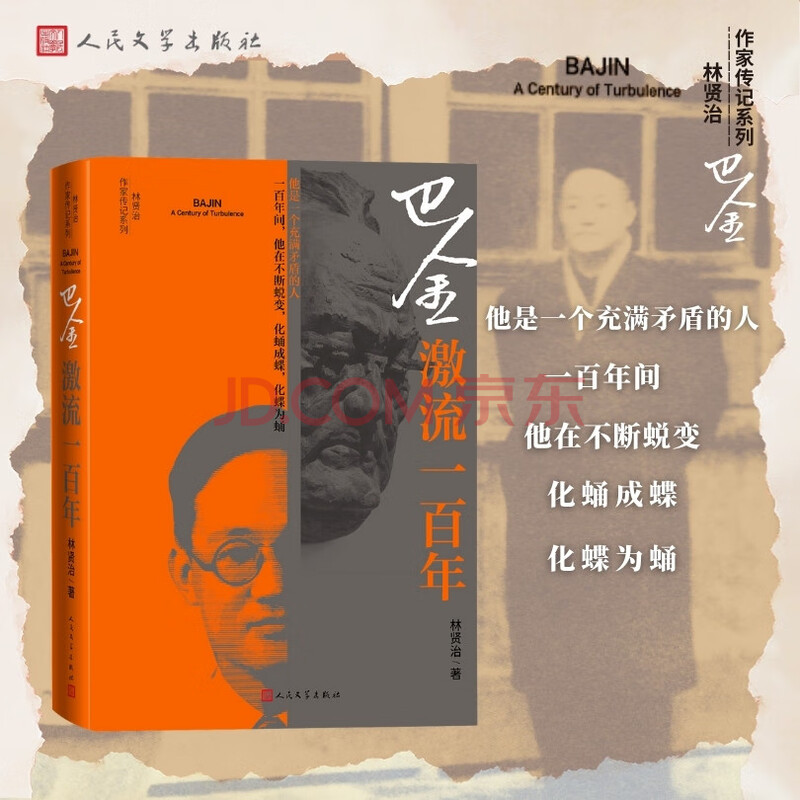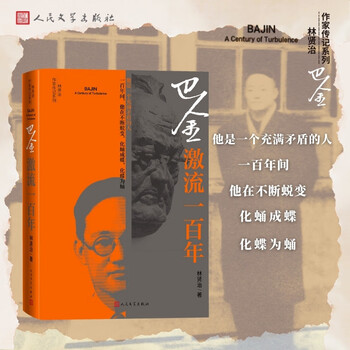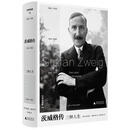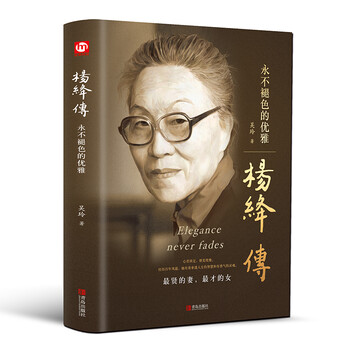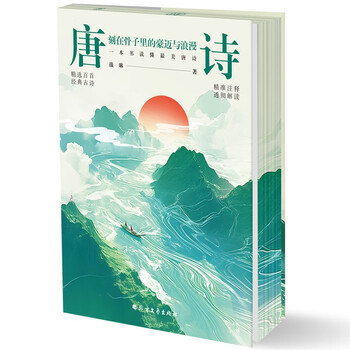内容简介
巴金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生中,巴金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不同时代的动荡与变迁。巴金自称是“‘五四’的儿子”,毕生不倦地追求着、反抗着、挣扎着、适应着又变化着。作者从史料出发,忠实地记录了巴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艰难的奋斗历程。
本书以巴金为经,以他的几位朋友为纬,贯穿多个历史事件,大起大落,动人心魄。书中,一百年逶迤道来,政治、历史、文学交相渗透,视野宏阔,材料翔实,夹叙夹议,跌宕有致,展现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图景。
精彩书摘
第二章(节选)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据说名字来自《诗经》中“蔽芾甘棠”的句子,有功业盛大的寓意。大哥尧枚,三哥尧林,他是末生子。十岁时丧母,三年后父亲病故。
大哥读中学时成绩优异,满心想着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然后留学德国。可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年替他完成了婚事,而且是用拈阄的方法决定的。婚后不久,父亲又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从此一房的生活重担由他一个人承担起来。由于压力太大,在接连的打击之下,他一度精神失常,三十四岁时便服毒自杀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巴金有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男女仆人多达四五十个。在巴金的眼中,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祖父是最高统治者,他用旧礼教把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维持一种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结果引来更多的仇恨、争斗和倾轧。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巴金就看见叔父们开会处分他的东西,还在他的灵前争吵,完全暴露了一个大家庭的冷酷与虚伪。青年人自由行动的权利遭到剥夺,犹如生活在囚笼里。在这里,巴金目睹了许多青春的生命在魔爪下挣扎、呻吟,被撕成碎片或者暗暗沦亡……
李公馆有两个世界,用巴金的说法,一个属于“上人”,一个属于“下人”。下人的世界在门房、马房、厨房里,由仆人、马夫、轿夫们组成。巴金常常到这里玩,在下人中间,感受人世的艰辛,接受最初的人道主义教育。他看见他们如何劳作、受苦、病死、吊死、被赶出街头。面对这位少爷,他们能诚恳地倾吐痛苦,坦率地批评主人,毫不隐瞒。巴金含着热泪凝视、倾听这一切,心里升起火一般的反抗思想。他发誓要做一个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的人。
巴金的少年时代不能说是幸福的。母亲的爱抚过于短暂。母爱固然教他爱人类、有同情心,但也使他变得敏感和脆弱,甚至懦怯。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父亲亡故的心情时,笔下依然保留了稚子般的依恋,说:“我心里更虚空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早年丧失父母,会增加患上一种叫“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可能性,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金这个曾经“被人爱着的孩子”,顿时有了压抑感和孤独感。他觉得包围他的唯是黑暗和恐怖。他失去了依靠,没有安全感,从此养成一种孤僻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喜欢向内心发掘,喜欢探寻问题的根底。所以,巴金看起来热情、明朗、易于冲动,事实上有着沉郁多思、善于克制、谨言慎行的另一面。比较起来他没有多少罗曼蒂克,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由于巴金怀有坚定的信念而缺少相应的意志力,故而寻求朋友,渴望倾诉。可以设想,他少时走向仆人群体中间,很可能带有取暖性质。他的早期写作,几乎都出于感情倾泻,有潜在的倾听者。在小说家中,他说他不喜欢卡夫卡,其中不无回避官方误解的因素,因为在“文革”以前,所谓“现代派作家”都被划归“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不过卡夫卡的写作确实与他不同,根本无须考虑读者,无须交流,那是彻底的为孤独而写作。
忧郁和孤僻,其实并不妨碍一个人采取激烈的行动。美国科学史家弗兰克·萨洛韦在著作中指出:后出生子女大都与头生子女易于屈从的策略相对抗,具有革命性的个性。可是,他又说:“家庭体系的某些特点会加强羞怯性格,这最常见于大家庭中的后出生子女以及那些在早期孩提时代就丧失了父母的人中。由遗传天性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身为后出生子女会引起相互矛盾的后果,它使一些人变得既有反叛性又很胆怯。”哥白尼在三个同胞中排行最小,沉默寡言,却大胆地提出“日心说”,推翻有史以来关于天体学说的定论,被称为“哥白尼革命”。就性格而言,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胆怯的教士”。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把巴金称为“胆怯的革命者”。
青年巴金确实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反抗者、革命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末生子的“乐于体验性”、叛逆、冒险、任性,反抗现状,挑战强权,不惮于自我牺牲。而所有这些,为一种英雄意识所统摄的特点,又都与内心的黑暗有关,本质上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正如巴金自我分析时说的:“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
应当承认,巴金从来不曾与专制政权发生过正面冲突。不出意外的是,在政治高压之下,他做出妥协,明显地向后退。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他不满于这种蜕变,他挣扎过、斗争过,为此感到痛苦,然而又满足于这种痛苦。就是说,他无法战胜内心的黑暗,乃至到了最后,当他回顾来路时,却又不无痛苦地发现,前后变化之大,简直连自己也辨认不出来。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新 潮
第二章 少年安那其
第三章 圣地法兰西
第四章 徘徊于文学与革命之间
第五章 烽火中
第六章 沉默中退守
第七章 大转折
第八章 在朝鲜
第九章 胡风集团案
第十章 多事之秋
第十一章 走近深渊
第十二章 十年一梦
第十三章 回归之路
尾 声
主要参考书目
试读
第二章(节选)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据说名字来自《诗经》中“蔽芾甘棠”的句子,有功业盛大的寓意。大哥尧枚,三哥尧林,他是末生子。十岁时丧母,三年后父亲病故。
大哥读中学时成绩优异,满心想着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然后留学德国。可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年替他完成了婚事,而且是用拈阄的方法决定的。婚后不久,父亲又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从此一房的生活重担由他一个人承担起来。由于压力太大,在接连的打击之下,他一度精神失常,三十四岁时便服毒自杀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巴金有近二十个长辈,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姐妹,男女仆人多达四五十个。在巴金的眼中,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祖父是最高统治者,他用旧礼教把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维持一种中世纪式的生活方式,结果引来更多的仇恨、争斗和倾轧。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巴金就看见叔父们开会处分他的东西,还在他的灵前争吵,完全暴露了一个大家庭的冷酷与虚伪。青年人自由行动的权利遭到剥夺,犹如生活在囚笼里。在这里,巴金目睹了许多青春的生命在魔爪下挣扎、呻吟,被撕成碎片或者暗暗沦亡……
李公馆有两个世界,用巴金的说法,一个属于“上人”,一个属于“下人”。下人的世界在门房、马房、厨房里,由仆人、马夫、轿夫们组成。巴金常常到这里玩,在下人中间,感受人世的艰辛,接受最初的人道主义教育。他看见他们如何劳作、受苦、病死、吊死、被赶出街头。面对这位少爷,他们能诚恳地倾吐痛苦,坦率地批评主人,毫不隐瞒。巴金含着热泪凝视、倾听这一切,心里升起火一般的反抗思想。他发誓要做一个同他们站在一起、帮助他们的人。
巴金的少年时代不能说是幸福的。母亲的爱抚过于短暂。母爱固然教他爱人类、有同情心,但也使他变得敏感和脆弱,甚至懦怯。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父亲亡故的心情时,笔下依然保留了稚子般的依恋,说:“我心里更虚空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但是一走到行人拥挤的街心,跟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有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早年丧失父母,会增加患上一种叫“过度换气综合征”的可能性,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金这个曾经“被人爱着的孩子”,顿时有了压抑感和孤独感。他觉得包围他的唯是黑暗和恐怖。他失去了依靠,没有安全感,从此养成一种孤僻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喜欢向内心发掘,喜欢探寻问题的根底。所以,巴金看起来热情、明朗、易于冲动,事实上有着沉郁多思、善于克制、谨言慎行的另一面。比较起来他没有多少罗曼蒂克,到底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由于巴金怀有坚定的信念而缺少相应的意志力,故而寻求朋友,渴望倾诉。可以设想,他少时走向仆人群体中间,很可能带有取暖性质。他的早期写作,几乎都出于感情倾泻,有潜在的倾听者。在小说家中,他说他不喜欢卡夫卡,其中不无回避官方误解的因素,因为在“文革”以前,所谓“现代派作家”都被划归“西方资产阶级作家”,不过卡夫卡的写作确实与他不同,根本无须考虑读者,无须交流,那是彻底的为孤独而写作。
忧郁和孤僻,其实并不妨碍一个人采取激烈的行动。美国科学史家弗兰克·萨洛韦在著作中指出:后出生子女大都与头生子女易于屈从的策略相对抗,具有革命性的个性。可是,他又说:“家庭体系的某些特点会加强羞怯性格,这最常见于大家庭中的后出生子女以及那些在早期孩提时代就丧失了父母的人中。由遗传天性和环境的相互作用,身为后出生子女会引起相互矛盾的后果,它使一些人变得既有反叛性又很胆怯。”哥白尼在三个同胞中排行最小,沉默寡言,却大胆地提出“日心说”,推翻有史以来关于天体学说的定论,被称为“哥白尼革命”。就性格而言,一位传记作家称他为“胆怯的教士”。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把巴金称为“胆怯的革命者”。
青年巴金确实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反抗者、革命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末生子的“乐于体验性”、叛逆、冒险、任性,反抗现状,挑战强权,不惮于自我牺牲。而所有这些,为一种英雄意识所统摄的特点,又都与内心的黑暗有关,本质上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正如巴金自我分析时说的:“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
应当承认,巴金从来不曾与专制政权发生过正面冲突。不出意外的是,在政治高压之下,他做出妥协,明显地向后退。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他不满于这种蜕变,他挣扎过、斗争过,为此感到痛苦,然而又满足于这种痛苦。就是说,他无法战胜内心的黑暗,乃至到了最后,当他回顾来路时,却又不无痛苦地发现,前后变化之大,简直连自己也辨认不出来。